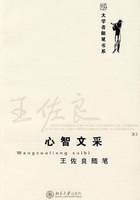
第2章 文学的伦敦,生活的伦敦
曾经有多少英国作家写过伦敦?或者不如问:英国文学史上,有哪几个重要作家不曾写过伦敦?我走在伦敦的街上,似乎听到过去英国文学作品中某些词句、某些段落的回响。似乎莎士比亚、琼生、狄福、约翰荪、盖依、狄更斯、济慈都在说话,还有小品文大家兰姆,还有20世纪写意识流小说的维吉尼亚·伍尔夫,等等。兰姆写过一封致友人书,说他如何常在晚上站在泰晤士河边大马路上看街灯下的过往行人,以此为乐,并且下了一个结论:“谁要是厌倦了伦敦,谁就是厌倦了生活。”
不只是英国作家在说话,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作家。我想起朱自清先生,他的《欧游杂记》里就有用纯净的散文写的关于英国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等处的篇章。
然而一个城市,如果仅仅靠过去的记忆而存在,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跟着朋友去参观狄更斯住过两年多(1837—1839)的家宅,在陶提街四十八号,一所三层楼的平常屋子,里面到处都是纪念品,连楼梯边的墙上也挂满了画和照片,屋子小而东西多,令人感到气闷。我只匆匆走了一个过场,赶紧出门透气。相片里的狄更斯神情肃穆,似乎并不快乐。楼梯边有一张他晚年的伴侣艾伦·特能的小相片,一个年轻的演员成了一个老作家的秘密情妇,她的神情似乎也不快乐。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城是有特殊魅力的,然而无地不广,屋子连着屋子,尽是人和物件。他自己也曾说过,这城市“只是一个大垃圾堆”,无怪乎他一有机会,总要让他的主人公骑马或乘车跑出城去,在那乡间大道上放开奔驰。只在那种时候,我们读者才跟着他自由自在地呼吸清新的空气!他的神来之笔,往往是在那些段落里。
济慈的故居则给我完全不同的感觉。一座白色的两层楼房,房间大而明亮,家具不多,起居室有落地长窗,看得见外面的草地和鲜花,靠窗摆了一把椅子,这就是诗人常常独坐思索的地方。楼上卧室里有一张挂着帐子的单人床,床单和枕头布洁白如雪。1820年2月3日晚上,济慈从伦敦城里回来,途中受了凉,到家赶紧上床,轻轻咳了一声,就在这洁白的床单上咳出了一滴鲜血。我看了床旁的文字说明,几乎不敢逼视那床单了。那么残酷的命运!那样早就从年轻诗人的心房里逼出了血,拿它染上了他那洁白的想象世界!
我不是第一次来此。三十多年前,我也是跟着一些同学来过这里。那时候,我已是济慈的诗的爱好者——哪个读英国文学的年轻人能不爱济慈呢?——但是我对他了解得很不够,注意力放在他同范尼·勃朗的爱情关系上,看过了这屋子里所陈列的她的小画像,也就像普通游客似的走开了。三十年后重来,我仍然未必真正了解济慈,但是我读他的诗和日记的时候多了,我自己经历的事情也多了,这才体会到济慈的锐气和深度。一个无名的青年作家,在种种不如意的情况下,向英国诗的新天地猛进。1819年他二十三岁,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全部最好的作品,包括那六首不朽的“颂歌”,而不以此为足,还要更拔一个高峰,写出了莎士比亚式的诗剧片断,直到肺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写的是当时最尖端的作品:美到了尖端,崇拜古希腊到了尖端,对人世灾难的感受也到了尖端。《夜莺颂》写得何等的美,然而诗人也在这里,写出了当时英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苦难:
这里众人呆坐,听彼此呻吟,
老人仅有几丝白发,瑟瑟抖动,
青年骨瘦如鬼,苍白而死;
只要想一想就充满哀伤,
更有绝望铅一般沉重;
明眸的美人难保一夜的风姿,
到明天只等得新欢来悼亡!
这首诗就是在这所屋子外面的花园里写的,时间是1819年5月。
我同陪我来的裘克安兄在这园子边上的一条长凳上坐了好久。那草地修剪得整齐,在阳光下一片碧绿;四边有几处花池,也是一片鲜艳;另外有两棵大树,给这园子带来了野趣,其中一棵桑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这园子离汉姆斯退特荒地很近,那是一片草木丛生的高地,济慈当年就是常到那里去听夜莺的歌声的。
我没有时间去汉姆斯退特荒地,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得尽量在伦敦西区公园里的草地上散步。从我旅馆所在的王后门街,几分钟就走到了堪星顿花园,那里就有大草地,与之相连的是海德公园,有更多更大的草地。英国式公园的特点就是有空旷的草地,不像法国式公园那样修饰得整整齐齐,拼成了大小若干块几何图案,而是不甚规则,大片草地往往连续几里,偶然有孤立的大树,有些地方还有圆池或长河,但没有多少人工点缀,而草地本身却十分引人,一来是草的质地高,厚而密,是多少年来培植经营的结果;二来它不是只为观赏,而是可以在上面散步,也可以坐着躺着,甚至打滚玩耍,一概无人干涉。这些草地不仅给伦敦城带来了野趣,而且使得伦敦人有一个地方可以闻闻青草和土壤气味,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我于是注意伦敦人的神态举止。像学生时代一样,我一到西欧名城,总是手执地图,按图寻求有名的街道、桥梁、建筑,能步行处总是步行前往。走累了我就进一家咖啡店或快餐馆临窗坐下,看过往行人。伦敦各区不同,但都有值得停留之处。虽然有了些高层建筑,但中心区大体仍是原状,只不过我感到屈拉福尔加广场等处比我记忆中的要小多了。我到的那几天,正值公共汽车和地下铁道罢工,所以街上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车的多半是年轻的家庭妇女,我站在街口看她们从我身边快踏而过,骑车熟练和灵活的程度不减北京的女同志们,阳光照耀在她们的脸上,脸色是愉快的。另外,我注意到街上亚洲人、西印度群岛来的人和阿拉伯人都明显增加。他们也都或庄严或活泼,在这西方大城里各操其业。
一百多年以来,伦敦就已是一个国际都市。我看到许多保养得很好的旧房子,如阿尔伯特大会堂,有名的高级百货商店哈罗兹,都有一种印度式的建筑风格,显示维多利亚女皇当年君临四海的神气。如今情况变了,伦敦城里树起了一些跨国公司的现代派高楼。在文化上,一位兼通科学与文艺的名人C。P。斯诺曾说,英国现在只以三种东西见长:一是自然科学研究,仍有英国科学家不断获得诺贝尔奖;二是安排大的典礼的能力,如国王加冕礼之类能组织得井井有条,而且形式美观;三是英国演剧仍然十分出色,仍然是吸引世界各处游客的大项目。
我也是关心英国戏剧的。所以当招待我的朋友们问我在伦敦特别想看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是:看戏,附带也看新的戏院。由于我的时间很紧,结果只能安排两次这类活动。一次是去参观了新近开幕的巴比肯中心。这里不仅有戏院、电影院,还有陈列室、图书馆、会议厅,以及供来开会的人住的两座大楼:一曰克伦威尔高塔,一曰莎士比亚高塔。在城区中间一小块地皮上,要安排这么一大片的房屋,可真费了英国建筑师的心血!我和裘克安兄去时无戏可看,只在里面走了一下,看见有一个印度歌舞团就在一处过道里排练,另一处过道的墙上展出了一个摄影家的若干幅作品。我们略事浏览,就到附设的餐厅吃午饭。近年新盖的外国大戏院总有两种方便观众的设施,即一个广大的露天咖啡座,和一个很像样但又价目公道的饭馆,而且两者都有很长的营业时间,没有服务员盯着让你吃完快走。
另一次是去国家剧院。7月8日下午6点,我刚从剑桥坐长途公共汽车回到伦敦旅馆,就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接待我的W女士的电话,说是晚上请我去国家剧院看戏,于是匆忙洗澡换了衣服就往外走。我从未去过70年代才建立的国家剧院,时间又紧迫,好容易在泰晤士河南岸找到了,又是一大片现代建筑,其中有大小剧场三个,还有书店、饭馆等附属设施。走了很久,好像一直在沿螺旋形的过道上升,最后才到达了那个中等大小的利特尔顿剧场。W女士在门口拿着票等我,两人赶紧入座,总算没有迟到,不一会儿就开幕了。
演的是一个喜剧,原名《恣意行乐》,作者是19世纪奥国演员兼剧作家约翰·耐斯特洛,现在经过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伯特改编,剧名也变成《大玩一气》(Tom Stoppard:On the Razzle)。斯托伯特是当代英国著名剧作家,在改编过程中对原剧做了很大变动,加重了性爱成分,对话中关于性的暗示和双关语大量出现。这种做法是目前西方常见的,就连莎士比亚的剧本也常有如此改编的。我看过邦特改编的《李尔王》,他把一个本来已经有不少残酷场面的剧本渲染得更是血淋淋的,另外就是突出性的勾引。同这类根本性的改编相比,斯托伯特的变动还是属于技术性的,还没有改掉原剧的19世纪维也纳情调,人们看到的仍是一位店老板当了市长之后向一位有钱寡妇求婚的中心情节,而其中最活跃的角色仍是一个叫做克里斯多弗的小学徒,并且按照传统他仍是由一位主要的女演员穿了男装来演的。
舞台上的布景仍是现实主义的,服装也有当年的中欧色彩,演技也符合英国传统,适度而不过火。剧的灵魂则在对话,改编者之功在此,演员之长也在此,真是爽脆灵活,速度极快,但仍字字清楚,说者似不费力,听者也不紧张。话剧毕竟主要是说话的艺术,喜剧更要求充分发挥口语的机智、活泼,这一点,那晚的演出是做到了。
看完戏,W陪我慢慢走下那盘旋的过道,一边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华特卢桥头。此处泰晤士河面特宽。桥上灯火辉煌,而对岸的许多大建筑都有泛光灯照明,一大排白色屋子临河而立,连倒影也壮观。我好像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幅伦敦夜景,不禁想起华兹华斯的一首十四行诗:
华特卢桥上口占
1802年9月3日
大地拿不出比这更美的风景,
谁能看到这一动人的奇观而不停留,
谁的灵魂就已迟钝。
……
当然,他写的是晨光中的伦敦,而我看到的是夜伦敦,时间不一样;但是立在同一座华特卢桥上,我感到我似乎对他当时的心情多了一分了解。
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又是忙忙碌碌,但我总算挤出时间到国家美术馆走了一趟。这里也是旧游之地,我首先看了近年来新购的名画,其中有一幅画面很大的莫奈的《睡莲》。莫奈画了好多幅《睡莲》,但据说现在伦敦所藏的是其中分外出色的一幅。它陈列在一间地位显著的房里,占了整整一面墙,果然是色彩淡雅,光影交错,写实而含象征意义,水乡宛似仙境。我也借此机会重看了过去喜爱的一些画家,如凡高、马奈、塞尚、戈雅,都有佳作,都仍然叫我停留好久。当然,这里陈列的英国画派的作品更丰富,从荷加斯的《卖虾女》、盖因斯波罗的肖像画一直到透纳的海洋景色。但我特别欣赏的是康斯退勃尔的《干草车》。这幅画画出了英国的乡村景色,一辆运干草的马车正过一条溪流,两个乡下人坐在车上,一个扬鞭赶马,一个注视着轮子在水中的走向,岸上近旁是大树、杂草,过去是草地,接着是树丛,后面则闪耀着一片金黄色的田野。它的复制品是美术书里常见的,但是今天看了原作,我才体会到它的画面之大,透视之深,给了我一种宽阔感。康斯退勃尔喜爱农村生活里的普通事物,曾说:
从磨房水坝流下来的水声,快坍的旧河岸,发亮的木柱,砖房——这些景象使我成了一个画家——我是感激的。
他的传记作者莱斯利也说:
我曾看他注视着一株杨树,欣赏到了出神的程度,就同他看见一个可爱的孩子要一下抱在手里一样。
仅仅说他喜欢大自然是不够的,而且对于他,大自然不是人迹罕见的高山大谷之类,而是乡村常见的景象:两个人赶车过河,一群孩子在水边钓鱼,长堤上一行杨柳,天空中几堆彩云。所以才画得这样真实、淳朴,又这样长远地吸住我们的灵魂。
这天最后一个约会,是去拜访我的老师威廉·燕卜荪教授。我已在几星期前在都柏林见到了他和他的夫人海塔,抵英后又收到了他们约我在7月9日去吃晚饭的信。他们住在伦敦西北区离汉姆斯退特荒地不远的地方。我从地铁车站出来,走向他们住宅时正在下雨,问了几次才找到了。一座两层楼的红砖房子,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雨一停,他们就请我坐在花园草地上喝起酒来,那时湿淋淋的树叶还在滴水,阳光把一切照得闪亮,空气新鲜极了。那几天伦敦相当热,雨一下也就凉爽了。
我进门之后,先把从北京带来的几样小礼物送给老师夫妇:两幅荣宝斋复制的吴昌硕的水墨画,以及我在不久前重返昆明时在石林买的白族的方巾和挂包。后者是给海塔夫人的,她对那些棉织品上的白族图案十分喜欢。她本人是一个雕塑家,吃饭之前还邀我参观了她的工作室,就在楼上,我看到了一些成品和半成品。燕卜荪先生本人对于吴昌硕不甚了然。一听说是比齐白石略早而且为他所佩服的人,就问:为什么那个时期中国出现了这样几个大画家,属于老传统而又各有创新?我说这问题我答不上来,只能提供一个情况,即两人都是又精篆刻与书法。
在座的还有一对客人,即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夫妇。马先生的汉语说得很好,他夫人则是原在成都生长的中国人。有两事凑巧:一是这对夫妇将与我乘同一班中国民航的飞机去北京;二是马先生说他曾译过我在昆明时代写的两首诗,收入他所编的瑞典文的《中国诗选》。
燕卜荪一家同中国的因缘是深长的。他本人1937年就来到正处于抗日战火中的中国。这时期他三十多岁,教书极认真,自己用打字机打教材,而且由于师生在流亡途中,图书奇缺,大部分材料,包括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整个剧本,都是他凭惊人的记忆力从脑子里拿出来的!同时他实行了导师制,同我们每个人当面讨论作文。他单身一人来到万里外的异国,生活条件艰苦而不以为意,还在南岳山里写出了关心中日战局的诗。1946年秋天他带了妻子和两个两三岁的孩子重来北平,我刚从昆明复员到了清华园,也带了妻子去看他们。记得有一次他同我坐在景山顶上,看着满城的秋色喝茶闲谈,他的两个孩子就在我们身边的山坡上爬着玩。
现在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已经成了汉语专家,中文名燕谋各,正陪着我们吃饭——不仅他本人,还有他的夫人和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原来我的老师的屋顶下,也是三代同堂了。
使人欣慰的是老先生研究的劲头还不小。他出自学院派,然而又能突破学院派的局限,因此他写的书总带开创性:青年成名之作《七类晦涩》开辟了诗义分析的新领域,50年代的《复杂字的结构》是后来西欧阐释派文论家引为先驱的大书,60年代的《弥尔顿的上帝》又破传统旧说并进而对教会一击,一直到几星期前他在都柏林纪念乔伊斯诞生百年的讨论会上驳斥美国教授和爱尔兰教士,他的建树又何止仅仅在“‘词的诗学’的演化”(乔治·斯泰纳语)一点上!他也是有名的诗人,作品少而精,有人说是写得太智理化了,谁想到在50年代又成了英国一群年轻诗人——即所谓“运动派”——竞相仿效的范本。他认为象征式的诗虽好,但已流行过久,所以主张要有一种辩论式的诗。他自己写的就是辩论式的诗。我想写诗的亲身经验对一个文学理论家是有好处的,而英国文学的长处之一正是由于有一连串的作家兼文论家,从17世纪的琼生、特莱顿,经过18世纪的浦柏、约翰荪和19世纪的华兹华斯、柯律勒治、雪莱、济慈、安诺德,直到20世纪的艾略特,构成一个独特的传统。这些人知道创作的甘苦,所以谈起理论来也有血有肉,见解精辟。
燕卜荪的可亲处还在于他毫无架子。他历来就平易近人,他在蒙自、昆明的宿舍和他后来在北京沙滩附近的家成了我们这些学生常去的地方。最近几年内,他得了一连串的荣誉:爵士封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英国学士院院士身份(F。B。A。)。这后者在英国公认为一位文科学者能得到的最高荣誉,要经过全体院士选举才给。那晚喝酒时,我笑着问他:“当了院士什么滋味?”他说:“没有什么意思。英国学士院搞关门主义。我写信给院长以赛亚·柏林谈这问题,他回信说确有关门主义。他们宁可拿钱去资助考古发掘之类的事,而不肯去帮助有才华的年轻人。”他自己则与此相反,总是尽力帮助年轻学者。我知道最近他还帮助一位中国中年学者取得了去牛津一个学院进修的机会。
他对于他教过的多少届中国学生是关心的。当我拿出一本北京出版的《外国文学》杂志的“莎士比亚专号”,告诉他哪几篇文章是他的老学生所写,而且这些人至今还在大学里教英语和英国文学,他那平素不露感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并且对在座的客人说:“这些人都是我去中国第一年教的学生。”
然而等我问他是否还想再去中国的时候,他却说:“恐怕不容易了。年纪太大了。我愿意把剩下的时间用来赶紧写书,还有几本书是我想写的。”
吃完午饭一直谈到快1点,我终于起身告辞了。他握住我的手说:“几时再见难说了。保重!”
燕谋各先生驾车送我回旅馆,在路上他表示感谢我这次去访他家。“今晚威廉的情绪多好,他多么高兴看见你们这些老学生!”
我说:“我们也高兴见他。他是我们尊重的老师,他也是我们青春岁月的一部分。”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