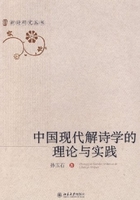
第7章 读诗解诗与“诗的思维术”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理论诞生之初,诗人穆木天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超前性的论点:建立“诗的思维术”。
穆木天是在反思以胡适代表的五四初期白话诗过分直白的缺点,努力探索诗与散文的界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的。在倡导“诗的朦胧性”理论的同时,他认为:“我们如果想找诗,我们思想时,得当诗去思想。”倘若是“先当散文去思想,然后译成韵文,我以为是诗道之大忌。我得以诗去思想Penser en Poèsie。我希望中国作诗的青年,得先找一种诗的思维术,一个诗的逻辑学。作诗的人,找诗的思想时,得用诗的思想方法。直接用诗的思考法去思想,直接用诗的旋律的文字写出来:这是直接作诗的方法”。
据我理解,这里讲的“以诗去思想”、“诗的思考法”、“诗的思维术”,不仅指一般的形象思维,而且指与散文(包括小说、散文等)的思维相区别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创作特有的独特性思维方式。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思维方式与传统诗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这一诗潮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也成为这一潮流的诗出现陌生化现象的根源。他们的感觉方式与思维方式的特点是:避去对于思想概念的依赖,往往以直觉作为可信的诗的呼唤,或发掘深层的内心飘忽不定的感悟,或捕捉刹那间的灵动与“客观对应物”的撞击,或用模糊的意象再现潜意识或是显意识的思绪,如何其芳说的一句话:“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这种思维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伸展、跳跃、活动的空间,模糊与不确定成为它的普遍特征。接受者对于这一类诗的难以理解以至误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进入这些诗人独特的思维轨道。
这里只着重探讨一个侧面,即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思维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玄想性和跳跃性。他们认为诗歌多是人们内心世界的潜意识的活动,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诗乃是主观的情感与“客观对应物”的一刹那间的契合物。这样,就给这种诗的思维带来了一种神秘的和隐藏的色彩。思维经过语言载体而出现的形态,已经经过他们思路的重新“编码”,便同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差异。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思维的超常性和陌生化,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扩大,因此是必然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匡正浪漫派诗一泄无余、过分袒露的毛病,象征派、现代派诗人有意识地追求直觉的感受和传达的朦胧。思维的极大的跳跃性,凝成诗的形态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意象与意象、语句和语句之间的空白。这些空白,不仅是语言的省略造成的,更主要是思维本身的跳跃、潜意识或显意识的非常规的联想,在意象和语言上产生的结果。与传统常规的思维相比较,我借用西方60年代以后流行的人类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再加上一点限制,可以称为是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创作中的“野性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
关于象征派、现代派诗人及其作品中这种“野性的思维”的特征,外国的一些诗人和批评家、中国30年代的诗人与批评家,都有过清晰的论述。
英国诗人与批评家T。S。艾略特,在批评理论上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他在英国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的作品中,找到了与19世纪到20世纪新兴的现代派诗之间存在的很多共同的特质。他在著名的论述玄学派诗人的几篇文章里面,非常清楚地谈到了这些玄学派诗人所具有的玄想式的思维特征。他认为玄学派诗人的思维特征之一,就在于“不是对比喻内容单纯的阐释,而是思想快速联想的发展——这要求读者具有相当的敏捷”。他引述了最早使用“玄学诗人”这个称号来批评这个诗人群体的约翰逊的话。约翰逊非难这些诗人,认为他们是将“最异质的意念强行栓缚在一起”。这种非难有它的合理性。但是,T。S。艾略特接着又申辩说:“素材某种程度上的异质可以通过诗人的思想而强行结成一体,这种现象在诗歌中比比皆是。”他认为,玄学派诗人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思维与诗句构建中特有的“机智”,是“成熟文学的一个品质;一种赶在英国思维变化之前扩散到英国文学中去的品质”。由于他们这种超越“英国思维”的品质的结果,“诗人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陌生的变得熟悉”。玄学派诗人的思维方式,为后来的象征派、现代派诗人们所借鉴。他们超越人的习惯性思维,以“快速联想”和“强行扭结”的方法,造成一种特别的艺术效应,即陌生化的效果,进入和理解象征派、现代派诗的障碍就由此而产生了。
李健吾先生在谈论废名诗歌的时候,对于思维空白的问题,曾经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为了某种方便起见,我不妨请读者注意他的句与句间的空白。惟其他用心思索每一句子的完美,而每一完美的句子便各自成为一个世界,所以他有句与句间最长的空白。他的空白最长,也最耐人寻味。我们晓得,浦鲁斯蒂指出福楼拜造句的特长在其空白。然而,福氏的空白乃是一种删消,一种经济,一种美丽,而废名先生的空白,往往是句与句间缺乏一道明显的‘桥’的结果。你可以因而体会他写作的方法。他从观念出发,每一个观念凝成一个结晶的句子。读者不得不在这里逗留,因为它供你过长的思维。”几乎同时,何其芳先生在回答有些人非难新诗的“晦涩难懂”的时候,认为对于现代派诗,“我们难于索解的原因不在作品而在我们自己不能追踪作者的想象。高贵的作者常常省略去那些从意象到意象之间的连锁,有如他越过了河流并不指点给我们一座桥,假若我们没有心灵的翅膀便无从追踪”。李健吾、何其芳所说的句与句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出现的“空白”或“连锁”,均与现代诗人和读者的思维特性有关。象征派、现代派诗人这种“野性的思维”,不是因为残缺不全,而是有意追求的结果。玄想或跳跃是造成这种“野性的思维”的主要手段。巧合的是,李健吾与何其芳两个人都说到了“桥”。思维与思维之间有断裂才有“桥”。这个“桥”,可以代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审美障碍,也是作品与读者之间沟通的纽带。作者的“过长的思维”,留给读者去自由地“逗留”、想象;作者过了河,却拆去了“桥”,让读者靠一种多向的思维去“追踪”;这本身,就是象征派、现代派诗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思维对接。阅读象征派、现代派诗,必须有这种“野性的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否则,便往往会产生对作品的隔膜和误读。
一次关于冯雪峰的诗《米色的鹿》的讨论中出现的分歧,很值得思考。《米色的鹿》写于上饶集中营的监狱中。诗的第一节,是写米色的鹿跳跃在黝绿的平野,是那么轻盈而美丽;诗的第二节,是写米色的鹿在波涛起伏的丛山和暗黑的森林之中生活、游戏,面对“陡削的悬岩”,和“下面深不可测的沟壑”,“而米色的鹿一跃就跃过”;诗的第三节却是一个复杂的画面:
但是,看!这也是多么好的一种景色!
太阳已经上升,而大地冻着一片的雪,
可是,多么美丽的荒野的雪地!
多么年轻的仆倒着的尸体!
他僵硬了的两手,还做着快跑的姿势,
他露出的半边的脸,还浮着不能收住
的青春的微笑;
而冬日早晨的太阳正在照着,
而终夜被逐的米色的鹿,在颤抖着,
在不远的前面喘息着……
这首诗写于1941年到1942年之间。那个时候,敌人惨无人道地随时杀害被监禁的革命者。多少青年死于无声的荒野之中。他们的英勇的姿态,他们的扑倒的身影,他们的不死的精神,时时在冯雪峰的头脑中闪现。生活力的冲动激发了他的诗情。象征诗的影响进入他的思维。在窒息一般的监狱中,又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便产生了这样既鲜明而又隐曲的诗篇。由此,对于该诗就产生了解读上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里运用了象征的方法,将战士僵硬的尸体与快跑的姿势,和米色的鹿的颤斗与喘息这两个十分鲜明的意象,叠印在一起,交互呈现,暗示出作者赞美与愤怒织就的情思。作者是用米色的鹿的象征性形象,来暗示被杀害的年轻战士的可爱、勇敢与无畏。另外有两种理解,就实了一些。一种意见认为,米色的鹿代表中国传统的“福禄寿”的“禄”,是权力者与牺牲者的对立;一种意见认为,米色的鹿代表“逐鹿中原”的鹿,是一种权力之间争夺的象征。我以为,后两种意见,对于诗的理解,都太死板,有些几近猜字谜,而不是读诗。这种过实的死板的理解,本身正确与否,并不是我所关注的。我所关注的,乃是产生这种过实过死理解的思考方式,与现代诗的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差异。现代性的“野性的思维”,带有多向性与流动性的特征。多向就会导致艺术意象的繁复与多义;流动乃是意象与意境模糊的根源。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两种心理原型的差异。
30年代中期,在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争论中,朱光潜先生依据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把各种人的心理原型分为“造形的想象”和“泛流的想象”两种,认为属于“造形类”的人们,不容易创作和阅读“迷离隐约”的诗,而属于“泛流类”的人们,不容易创造和欣赏“明白清楚”的诗。值得补充的是,人们这种心理原型上的差异,又是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分开的。具有多向性与流动性的“野性的思维”的人,也就在创作与欣赏上与“迷离隐约”的诗有天然的联系。朱光潜先生在这篇论文中还进一步说:“修养上的差别有时还可以用修养去消化”,而不容易消化的差别,乃是诗人与作者之间存在的“心理原型上的差别”。象征派、现代派诗的接受,与它的创作一样,是一种很繁复又很纯粹的心理和思维活动。接受者与欣赏者,如果离开心理与思维的差异,而在诗歌本身寻求普遍的价值标准,或以自己的习惯性思维进入现代性的创造思维,总不免隔靴搔痒,或走入误读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