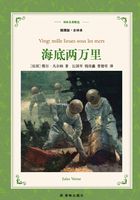
三 先生,悉听尊便
在收到霍布森的来信之前,我出征追剿独角鲸的欲望还没有试图穿越美国西北部的念头那么强烈。一读过这位尊敬的海军部秘书的来信以后,我最终明白了自己的真正志向,我一生的惟一追求,便是追剿这只令人类不安的海怪,把它从这个世界上清除掉。
可是,我刚刚完成了一次艰辛的旅行,疲惫不堪,只想休息。我只盼着早点回到自己的祖国,跟朋友们重逢,入住我那位于植物园里的小屋,欣赏自己心爱的珍藏!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我忘却了一切:疲惫、朋友,珍藏。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何况,”我心里想,“条条道路通欧洲。兴许,独角鲸还挺友善的,能把我带回到法国海岸!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有可能在欧洲海域里被我们擒获——是为了自己高兴——我可要为巴黎自然博物馆带回不短于半米的戟状獠牙。”
可在这之前,我得去北太平洋寻找这条独角鲸。这与我回法国的路程可谓是南辕北辙。
“龚赛伊!”我不耐烦地喊道。
龚赛伊是我的仆人。这可是个忠心耿耿的小伙子,一个正直的弗莱米人。我每次出门旅行,都有他陪伴左右。我喜欢他,他也知恩图报。他遇事冷静,做人规矩,待人热心,对生活中发生的意外很少大惊小怪。他双手灵巧,什么都会做。虽然他名叫龚赛伊,要不是别人问他,他从不主动出谋划策 。
。
由于经常同我们巴黎植物园这个小圈子里的学者接触,龚赛伊逐渐学到了一些知识。我简直把他当成了一位专家。他非常精通博物学分类,而且能够以杂技演员的娴熟灵活把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等分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也就这么点学问。分类,就是他的生活,其他方面却知之甚少。他对分类学理论十分投入,而对实践却不大感兴趣。我想,他恐怕分不清抹香鲸跟一般鲸鱼的区别!然而,这确实是一个正直、能干的好小伙子!
十年来,我科学考察走到哪里,龚赛伊就跟随到哪里,从不计较旅途遥远和辛劳。无论前往哪个国家,是中国还是刚果,不管旅程多么遥远,他从无怨言,提起旅行箱就走;去哪里都一样,他从不多问。而且,他身强力壮,肌肉结实,能抵抗任何疾病;他既不冲动,也不恼火,为人随和。
这个小伙子那年30岁了,同主人的年龄比是15:20。各位读者,请原谅我用这种方法来交待自己的年龄。
只是龚赛伊有一个缺点:太拘泥于礼节。他总是用第三人称跟我说话,简直令人讨厌。
“龚赛伊!”我又喊了一声。这时,我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起行装来。
当然,我非常信任这个忠心耿耿的小伙子。平时,我从来不问他是否愿意跟随我去旅行。然而,这回可不同于往常。这次远征没有确切的期限,有可能会无限延长,而且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行动,是去追剿一头撞沉一艘驱逐舰就像砸碎核桃壳那么轻而易举的动物?世界上最沉着镇静的人对这次旅行也得考虑再三!龚赛伊会怎么说呢?
“龚赛伊!”我第三次叫他。
龚赛伊终于露面了。
“先生,叫我吗?”他进来时问道。
“是的,小伙子。快帮我准备一下,你自己也准备准备。我们两小时后出发。”
“悉听尊便,先生。”龚赛伊心平气和地答道。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把我所有的旅行用品——外套、衬衣、袜子装到我的箱子里去,无须计数,不过尽量多带一些。要快!”
“那么,先生收集的标本怎么办?”龚赛伊提醒道。
“以后再说吧。”
“什么?先生的那些古兽、始马属等标本,以及动物的骨骼,怎么办呢!”
“寄存在旅馆里吧。”
“可先生的那只活鹿豚呢?”
“我们不在的时候,请别人喂养。另外,我会托人把我们的那群动物运回法国去的。”
“那我们不回巴黎了?”龚赛伊问道。
“回,当然要回去,”我支吾道,“不过得绕道。”
“只要先生愿意。”
“哦!小事一桩!只不过稍微绕点儿道。我们去搭乘亚伯拉罕·林肯号。”
“先生觉得好就行。”龚赛伊平静地回答说。
“朋友,要知道,跟那只海怪有关……就是那条出了名的独角鲸……我们要把它从海洋里清除掉……两卷四开本著作《海底奥秘》的作者,是不能不随法拉格特舰长出征的。这是一个光荣的使命,不过……也是一个危险的使命!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里!这些海怪也许非常任性!但我们还是得去!我们有一位勇敢的舰长!”
“先生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龚赛伊回答说。
“好好想想再说!我什么也不想瞒你。说不准,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行!”
“听先生的。”
一刻钟之后,我们的旅行箱收拾好了。龚赛伊干这种活易如反掌。我敢肯定,什么都不会遗漏,因为这个小伙子整理衬衣和外套,就像对鸟类动物或哺乳类动物进行分类一样在行。
旅馆电梯把我们送到中二楼前厅。我下楼梯来到底层。我在始终围满客人的大柜台前结清了账。我委托把一包包填塞好的动物标本和风干的植物标本运往巴黎。我还留下足够的钱托人喂养我的鹿豚。我跳上了一辆马车,龚赛伊跟在我后面。
这趟车费是20法郎。马车由百老汇大街一路驶到合众国广场,又沿第四大街行驶到与鲍威利街交汇的路口,拐入卡特林街,一直行驶到第34号码头停下。然后,卡特林号渡轮连人带车、马把我们一起送到了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属于纽约大区,位于东部河的左岸。几分钟后,我们便抵达亚伯拉罕·林肯号驱逐舰停泊的码头。林肯号驱逐舰的两根大烟囱冒着滚滚黑烟。
我们的行李立即被搬到了林肯号的甲板上。我匆匆登上了驱逐舰,询问法拉格特舰长在哪里。一名水手领我登上艉楼,来到一名神采奕奕的军官面前。他向我伸出手来。
“是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吗?”他问我说。
“正是,”我回答说,“您就是法拉格特舰长吧?”
“是的。欢迎您,教授先生!您的客舱早就准备好了。”
我向舰长告辞,好让他专心致志地备航。我由别人领着来到为我准备的客舱。
林肯号是为了新用途而精心挑选和改建的。这艘高速驱逐舰装备了过热装置,能使蒸汽增加到七个大气压。在这个压力下,林肯号驱逐舰平均时速可达到18.3海里。这个速度十分可观,但仍不足以同那条巨大的鲸鱼搏斗。
驱逐舰的内部装备符合这次远征的要求。我对自己住的房舱十分满意。它位于舰艇后部,面对军官休息室。
“这儿挺好的。”我对龚赛伊说。
“先生,请别见怪。”龚赛伊回答说,“就像寄居蟹钻进了蛾螺壳一样舒服。”
我让龚赛伊拾掇好我们的旅行箱,自己则重新登上甲板,看他们做出航前的准备工作。
这时,法拉格特舰长正下令松开将林肯号拴在布鲁克林码头上的最后几根缆绳。如此看来,我要是迟到一刻钟,甚至更短的时间,林肯号驱逐舰不等我就会起航,我也就错过参加这次非同寻常、令人难以置信、具有传奇色彩的远征的机会了。然而,将来可能还会有人对这次远征的真实记录持怀疑态度。
法拉格特舰长连一天甚至一个小时也不愿耽搁,急着赶赴不久前海怪出没的海域。他叫来了舰艇上的轮机长。
“压力够吗?”舰长问道。
“够了,先生。”轮机长回答说。
“起航!”法拉格特舰长大声下令道。
这道命令通过压缩空气装置传到机舱。接到命令后,机械师们立即启动机轮;蒸汽呼啸,涌入半开半掩的进气阀。水平排列的长长的活塞此起彼落,乒乓作响,推动着主轴的摇杆。螺旋桨的叶片连续拍打着海水,而且不断加速。林肯号驱逐舰在满载前来送行的观众的渡轮和小汽艇的“夹道”欢送下庄严地驶离港口。
布鲁克林码头和纽约东部河沿岸的街道黑压压地站满了好奇的人群。50万人发自肺腑的三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成千上万条手帕在密集的人群头顶挥动,表示向林肯号致敬,此般情景一直延续到林肯号行驶到哈得孙河口纽约城所处的长形半岛的尖端。
哈得孙河右岸别墅星罗棋布,风景如画;林肯号驱逐舰沿着新泽西州一侧顺流而下;两岸要塞林立,纷纷鸣炮,向林肯号致意。林肯号则连升三次美国国旗还礼,国旗上39颗星在驱逐舰后桅斜桁上闪闪发光。接着,林肯号改变了航速,驶进了有航标指示的航道。航道沿着桑迪·霍克沙洲顶端形成的内港划了一道弧线。当驱逐舰驶近沙洲时,再次受到成千上万名观众的欢呼。
由渡轮和小汽艇组成的欢送船队一直尾随着林肯号驱逐舰行驶,直到标志着纽约港入口的两座灯塔为止。
此时,正好是下午三点。领航员离开林肯号,登上一艘小艇,朝着停泊在下风口等待他的双桅纵帆船驶去。炉火烧得更旺了,螺旋桨加快了打水的节拍,林肯号沿着长岛低平、黄色的海岸行驶。晚上八点,火岛的灯光被甩在了西北方,林肯号在黑茫茫的大西洋洋面上全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