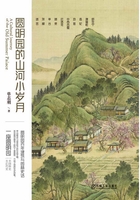
第一节 雍正对圆明园之扩建
雍正帝开启了后世皇帝在圆明园理政居住的先河与传统。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开始在圆明园南墙外增建处理朝政和举行典礼的宫殿衙署。自此,圆明园成为继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之后第三座兼具“圆苑”和“宫廷”双重功能的离宫型皇家园林。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规模从原来的600多亩变成3000余亩。雍正帝勤于政务,为了保证自身安全,除了不得已外出参加祭祀活动以外,平生极少离开京城,大多居于圆明园内,治理天下。
雍正时期,圆明园之南开始布局规划,建立坐北朝南的朝堂。大宫门面阔5间,门前设大型月台。进入大宫门,主建筑是位于圆明园中轴线上的正殿正大光明殿,雍正帝在此上朝。正大光明殿之东为勤政殿,是皇帝日常办公之所。为规范管理朝臣,雍正帝专门规定了官员们在圆明园的办公时间。
为召集廷臣到圆明园议政和办事,雍正帝制定了轮流奏事制度。因各衙门每天奏事多少不一,有的奏事多,有的无事可奏,所以雍正帝规定此后八旗遵循八天制,每天有一旗奏事,依次轮流。部院衙门也是每天有一个机构奏事,六部之外的都察院和理藩院同一天奏事,内务府也轮班一天。其他衙门奏事附加于部院之后。这样,每天都保证有一旗、一部来圆明园奏事,其他不当值奏事的衙门即便无事可奏,也要派堂官到圆明园,以备皇帝临时召见和交代事情。此外,为防止特殊情况发生,皇帝规定如果各部院和其他机构遇到紧要事件,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不必遵守已经排定的班次。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为父母服丧三年完毕,于正月十三日正式搬进圆明园。当时正值元宵节临近,王公大臣们向迁居圆明园的皇帝赠送了3000对灯笼表示祝贺。正月二十日,雍正帝在勤政殿等待大臣奏事,但一整天都无人面圣启奏,让雍正帝备感失落。为杜绝臣下反对他进驻圆明园,雍正帝立即向六部发布谕旨,此诏书标志着雍正帝正式宣告圆明园成为紫禁城外的又一政治中心。此后,群臣按雍正帝的诏书意愿将圆明园作为正式朝堂。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开始扩建圆明园,主要是建造朝堂和朝房等,以将圆明园变成除紫禁城之外的另一政治中心。

勤政亲贤遗址

今勤政亲贤之景
雍正帝将朝堂设在京西圆明园里,因此大臣们上朝颇为吃苦,经过雍正帝的督促和严厉批评,大臣们逐渐习惯了在圆明园里处理政务。雍正帝考虑到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特准年事已高的老臣不必来圆明园早朝。为了避免日复一日的舟车劳顿,许多官员开始在圆明园周围购置府邸,雍正帝也将附近的一些园林赐给亲信大臣,于是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为主的园林景群。
正大光明殿为圆明园正殿,外部建筑朴实无华,以与整座园林的风格相匹配;有殿堂七间,中殿悬有雍正帝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额;殿内装饰则金碧辉煌,以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雍正帝在正大光明殿举行日朝上朝、生日朝贺、庆贺节日、赐宴亲藩、宴请廷臣,还在此举行过大考翰詹、散馆乡试与复试。

正大光明
雍正帝亲手在正大光明殿书写的巨额匾联为:“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此联表达了雍正帝园居的双重目的为治国与休闲并举。雍正帝认为圆明园的宜居环境让他心旷神怡,有利于他更好地处理政务,而处理好政务才能使他性情更加愉悦,所以,园居理政有利于他的生活和工作形成劳逸结合的良性循环,最终达到提高办公效率的目的。
雍正帝平时多在勤政殿中召见大臣讨论政务和批阅殿试考卷。勤政殿,又称“勤政亲贤”,位于正大光明殿东,有五间殿堂,四周花木繁茂。
雍正帝每天在圆明园中处理政务的方式与在紫禁城处理政务完全一样。在圆明园中生活,既享受了园居乐趣,又需要高效率地处理日常政务。为此,雍正帝在勤政殿中题写“无逸”匾额来勉励自己处理好勤政与享乐的关系,让园居之乐促进而非妨碍公务。正如他自己所说:“白天接见大臣,晚上批阅奏章,时刻不忘效法父皇的勤政精神。”雍正帝在勤政殿中写下了不少诗篇来勉励自己不要因为贪图安逸而疏于政务。
雍正六年(1728年)一个闷热的夏夜,雍正帝在勤政殿处理奏章时,写下一首诗用以自警,其大意是说:我不想批阅奏章,想休息一下,但看到墙上高挂的箴言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愿浪费时间,即使酷暑时节也要日理万机。虽然园中乐事颇多,但我还是顾念国事民生。望见窗外半轮洁白的月亮,它好像告诫我要戒满戒躁。既然雍正帝在暑天都不能暂时放下政务到园中休息一下,那么一年四季,特别是春景热闹之时,他也未必能抽出足够时间尽情欣赏园中景物了。

九州清晏遗址
雍正帝在要求自己勤政的同时,也不允许臣下偷懒。雍正六年二月,御史鄂文善和曾元迈刚到圆明园值班,但常常还没到规定的时间就溜回城里的家中。雍正帝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应予重罚,以儆效尤,以告诫其他大臣不能懒惰。因此,雍正帝拒绝大学士提出的将二人交部议罪的常规方式,命令他们在每天日出之前便赶到圆明园宫门等候,日落之后才可回家,大大延长了他们在圆明园值班的时间。此后,再没有人敢擅自无故早退了。
雍正帝规定,凡三品以上官员都有给皇帝递送奏折、报告政务的权力,因此上千名京内外官员每天上呈的奏折和密折最多时竟达千余件,每天都要审阅并及时批示回复。雍正帝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借着昏黄的烛光批复堆积如山的奏折。据说这样大的工作量使雍正帝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只有在万寿节那天他才会睡个好觉。在他执政的十三年里,批阅过的奏折达四万份之多。

勤政亲贤
雍正帝在勤政殿墙壁上刻写自己手书的文章,表明治国安邦的坚定决心,要以祖辈为榜样,维护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为加强皇权,雍正帝还取消了诸王对下五旗(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军队的控制。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专门挑选职位较低、权力较小的大学士、学士等人作为自己的秘书班子。此外,他还一改康熙年间对待官员的宽仁政策,以严厉手段遏制康熙末年贪污腐化的风气,严惩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员。
作为雍正帝的私属园邸和常住花园,圆明园见证了雍正帝上演的腥风血雨、骨肉相残的政治斗争。
雍正帝非常重视圆明园的安全护卫。雍正为皇子时,园内有620名绿营士兵(180名骑兵和440名步兵)。雍正二年(1724年),圆明园内驻扎的士兵增至1000人(200名骑兵和800名步兵)。

山高水长
雍正三年(1725年),圆明园内建成练兵场。为提高士兵守卫圆明园的责任心和积极性,雍正帝每年给每名守卫圆明园的士兵发放20两白银的额外奖金。后来,随着圆明园地位的上升,圆明园的八旗护卫兵力达到3232人,所有官兵都是从满洲八旗中挑选出来的武艺精湛的士兵。这支御林军最终固定为3256人,包括136名军官和3120名士兵。他们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保卫圆明园的日常安全,二是在特殊节日增援皇帝身边的侍卫。这些侍卫平日在“山高水长”训练骑马和射箭,雍正帝偶尔也会视察军队操练。每逢农历六月的第十八天,圆明园都会举行“跑御马”活动,雍正帝在圆明园北墙外观赏御前侍卫的策马比赛。一个侍卫牵着两匹马,自己骑着一匹马,另一匹马在旁边;跑马过程中,这名侍卫会鞭策旁边的那一匹马,让它加速奔跑,同时侍卫会跳到另一匹快马的背上。侍卫如果能从后面跳到前方正在奔驰的马的背上,就能得到最高的奖赏;如果一名侍卫能成功地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并行的马的背上,即可获得二等奖赏;侍卫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马的过程中如果失败坠地,会从皇帝那里得到鼓励性的赏赐。雍正帝之后的历任皇帝,除咸丰帝之外,都沿袭了这一传统。
雍正帝在圆明园中度过了大半生的时光,沉浸于观赏日出日落、静心阅读写作的从容气氛之中。他平日喜欢和王公大臣在殿堂或斋阁里高谈阔论、品茶赏花。每逢节日,雍正帝还会带领亲信王公大臣到福海泛舟,以联络君臣感情。他们乘坐华丽的龙舟,后面跟着30艘船组成的船队。
福海不仅令雍正帝感到愉悦,还曾是他的避难之地。雍正八年(1730年)秋,一场地震不期而至,圆明园也遭到严重波及,很多建筑物倒塌。无处可去时,福海成为雍正帝的避难之地。地震当天,雍正帝逃往福海龙舟上避难,在船上度过了一整夜,福海由此成为他的福地。地震结束后,雍正帝不敢立即回宫殿里居住,便带着皇室成员在宫殿外空地上的大帐篷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在所住帐篷里接见了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如同其他帝王一样,雍正帝也把地震看作是来自上天的警告,连忙发布罪己诏,希望获得上天的宽恕和保佑,继续佑护他和大清江山。

1.蓬岛瑶台冬季

2.蓬岛瑶台小亭

3.蓬岛瑶台
雍正帝对于官员呈送的礼品也喜欢具体指导,或是对内务府承制的各种用具提出自己的设计意见。雍正八年(1730年),内务府总管海望拿出一件黑底珐琅五彩流云玉兔秋香鼻烟壶呈献给雍正帝。雍正帝指出鼻烟壶图案中的玉兔不好,其余可以照样烧制。海望又呈上一件桃红色底珐琅画牡丹花卉鼻烟壶,雍正帝看后,指出上下云肩与山子不太合适,需加以改动,其余花样不变。
在勤政殿的东院设有收藏工艺品和各类贵重物品的仓库。有的仓库专门存放景泰蓝;有的专门存放玉,包括用玉制成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有的专门存放来自欧洲的各式钟表,这些钟表装饰有宝石、玉石、金银等;有的专门存放各种精致衣物和绣品。其中,西洋样式的仪器和物品是雍正帝的兴趣之一。
雍正帝体验过西式服装,至今故宫中尚保留他的这幅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自己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
眼镜最早出现于1289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欧洲人的一项重要发明。雍正帝很喜欢西洋眼镜,倒不是他附庸风雅,确实是他已经眼花了,需要眼镜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材质有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等。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雍正帝经常起居的紫禁城与圆明园的宫殿里,甚至在他的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把眼镜发放给泼灰处的工匠,作为一种实用的福利待遇。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令内务府仿造“通天气表”(温度计)和西洋日(古代测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下令仿造望远镜,当时称之为“千里眼”。雍正八年(1730年),西洋耶稣教士远道带来仪器献给雍正帝,雍正帝十分喜爱,就让造办处的中国工匠仿制或者改装洋器。
很多时候,雍正帝就像迷恋游戏的儿童一样,穿着奇装异服,装扮成各种类型的人,愉快地优游于圆明园中。画师们就绘制有多幅雍正帝在圆明园中娱乐的图像。雍正帝喜欢到宫廷画室如意馆观看画师绘画。“如意馆”画师们以此为题材,为皇帝绘制了不少日常生活的写真作品。
雍正年间,在中国的传教士都遭遇厄运,唯有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受到特殊礼遇。这一时期,郎世宁创作了很多画作,如雍正元年的《聚瑞图》、雍正二年的《松献英芝图》等,都显示了他浓厚的艺术功底,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在宫廷之外,郎世宁还与雍正皇帝的几个同父异母弟弟关系颇为密切,如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为他们作画,并有多件作品流传至今。如《果亲王允礼像》《八骏图》横幅、《马图》册等。这些作品与现象证实了郎世宁在宫廷之外频繁的艺术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当时的贵族圈子里,玩赏欧洲风格的艺术品是当时流行的时尚。

洞天深处
雍正帝自幼勤奋好学、涉猎百科,他除了精通儒家经典并对佛道两家都有深入研究外,还对星象、占卜、堪舆、相面、算命等一类杂学进行过钻研。雍正帝尤其偏爱文化学术,在书法、陶瓷、园林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雍正帝深受康熙皇帝的影响,在四十余年的皇子生活中,潜心于读书、研经、作诗和习字。他曾泛临历代法帖,摹学二王、王厜、钟繇、颜真卿、蔡襄、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诸家之作,他善于模仿和体会,又能融会贯通,曾得到父皇的嘉奖。
圆明园大宫门东南角的“洞天深处”是诸皇子拜师学习的地方,这里距如意馆近,也可向“如意馆”画师们学习。几排教室和宿舍隐藏于竹林、兰花、松柏之中。乾隆帝为皇子时,每天上午都和兄弟们一起在此上课。弘历非常聪明,每天学习的内容都能背诵如流。他的师傅福敏常常跟他说今天的功课学习完了,还可以预习一下明天的课文。
雍正特意安排皇子住在圆明园里读书、生活,他们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学习儒家经典,二是学习满文、蒙文,三是学习弓箭、骑射。
雍正时期确立了皇子入学仪式,以后渐渐臻于完备并形成定制。皇子入学后,首先到上书房东次室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叩见礼。拜完孔子后,行拜师礼,正式拜认师傅。师傅坚决辞让,不敢接受拜见,皇子即象征性地向师傅行长揖之礼;师傅则郑重地将文房用品交给皇子,正式的师生关系就此确立。师生关系确立之后,无论何时相见,都要行师生礼。雍正为了弘历能得到更好的教育,特令他在圆明园内修身养性,并为他精心挑选了朱轼作为师傅,足见对弘历的重视。
雍正帝还为弘历选了一位师傅蔡世远专门教习古文。除了学习儒家经典以及满、蒙文外,雍正帝还非常重视皇子们的骑射技能。他要求皇子们每天下午到“山高水长”练习步射、骑射、刀术、剑术,并为他们选取了来自新疆的优良马匹。
雍正帝一生很少离开圆明园,即位后,在圆明园内特意仿《桃花源记》的境界规划“武陵春色”,用心良苦。雍正帝经常来此观赏日落景色,摆脱俗事牵绊。某个七夕节那天,在日落之后雍正帝仍然待在这里,率领后妃、子女以及其他近支宗室人员举行盛宴,观看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的佳景。这个节日也让他怀念已逝的年贵妃(敦肃皇贵妃)。

武陵春色之桃花洞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备受雍正帝宠爱的年贵妃于圆明园病逝。雍正帝非常悲伤,深深自责于自己忙于政事,没时间亲自照看年妃,致使年妃病情贻误,于是诏令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人员五日不跳神、不还愿,均为年妃穿戴孝服,四品以上官员及有封爵者一律到圆明园安奉年妃。大臣为年妃守孝时,需摘掉帽缨以示哀戚。雍正帝追封年妃为皇贵妃,谥肃敏。年妃育有三子一女,但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雍正帝与年妃情分最笃,因此在年妃死后才赐死她的哥哥年羹尧,且并未株连年妃的父亲及另一兄长。
雍正帝急于实行秘密建储,是在十分恐怖、紧张的政治背景之下实施的,与那时的年羹尧事件也有一定关系,是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担心,“以备无虞”而设立的皇位继承制度。雍正帝登基之初,就在紫禁城和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分别留下一份密诏,钦定弘历为合法继承人,确保万一自己突然辞世,朝政大局不致动荡。
雍正帝本人在骨肉相残的储位争斗中,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心力交瘁。当他将对手一个个消灭,自认为知情人也一个个离开人世后,长期紧绷的心弦猛然松垮,又突然发现对手的影响根本消除不了,因此精神与心脏都有可能难以承受。雍正八年那场大病也许就是前兆!雍正帝即位就预立储君,雍正八年大病之后两次向重臣提起立储君之事,这是他想要用稳定储位来减轻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同时确保自己遭遇不测时政权能够稳定交接。
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身患重病,感觉自己活不长久,便将圆明园内存放密诏的具体位置告诉了亲信大臣张廷玉。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再次将圆明园所藏密诏的位置告诉张廷玉和鄂尔泰两位重臣。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突然去世,被召进圆明园的大臣们立即取出秘密诏书,皇子弘历名正言顺地在圆明园内继承大统,然后护送雍正帝灵柩返回紫禁城。
雍正帝在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很高,在圆明园的布局理念中自有其独特之处。雍正帝胸怀大志、不露声色,熟悉历代所建造的苑囿和别业,不效法先人,并从经营自家花园开始,不去寻求古典园林的境界。
雍正时期的圆明园中,九州在宫廷区的北面,它以约200米见方的后湖为中心,环绕九个小岛,园林景观分九个区域。这“九州”分别为:“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在这个区域的核心地段,开辟近乎方形水面,九州围绕,如铜钱镶嵌在圆明园中,构筑成了九州之境。这是为“大一统”的太平盛世铺路,是文化与政治思想的认同。

杏花春馆

汇芳书院

濂溪乐处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汇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