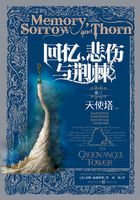
第4章 千叶千影
出逃之后,米蕊茉和西蒙已在森林里过了一周。这段旅程既缓慢又艰难,但米蕊茉在行动之前便已决定,宁可浪费时间,也不要被人抓住。整个白天,他们都在密密匝匝的树丛和混乱纠缠的灌木中挣扎,牵马的时间比骑马更长,惹得西蒙怨声载道。
“高兴点儿。”有一次,他们背靠一棵老橡树,在空地上休息时,她对他说,“至少这几天还能见到阳光。等离开森林,我们就得在夜间上路了。”
“至少在夜间,用不着担心有东西会划伤我全身的皮肤。”西蒙怒气冲冲地回嘴,揉搓着破破烂烂的马裤和底下的擦伤。
米蕊茉发现,有事可做确实令人振奋。紧缠她几周不放的无助感消失了,现在她又能清晰地思考了。她又能看清周围的一切,就像换了双新眼睛……还能享受与西蒙共处的时光。
她确实很享受他的陪伴,有时甚至希望自己别这么享受。但她骗了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她离开约书亚叔叔,动身前往海霍特,却没告诉他全部理由。另外,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纯洁了,再没资格与其他人永结同心。
都怪阿庇提斯,她心想,对我做了这种事。要不是他,我还是别人心目中的处子呢。
但真是这样吗?他并没有强迫她。是她放任他为所欲为的——在某种程度上,她曾经接受了他。阿庇提斯最后露出了禽兽的嘴脸,但在她床上时,他与世上大部分拥抱爱侣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并未强暴她。如果他们的行为有错又有罪,那她自己也要负上同等的责任。
可这一来,西蒙又怎么算呢?她的脑子有点乱。他不再是个男孩了,而是个男人。正是这一点让她有些害怕,恰如她害怕其他男人一样。但她又觉得,他身上依然保留了一些纯真的特质。他急切地想把事情做对,被她亏待后又难掩内心的伤痛,简直就是个大男孩。看到他一心为自己着想,却完全猜不中自己的心思,只让她觉得更加难过。正因为他对自己这么好,正因为他对自己的欣赏和赞美,才让她忍不住想要发火,就像他对真实的她故意视而不见似的。
这感觉有些可怕。好在西蒙似乎也明白,自己的真情对她是种痛苦,因此便又退回到嘻哈打趣的朋友关系,好让她自在些。当待在他身边又不用考虑身份时,她发现他确实是个不错的旅伴。
虽然在祖父和父亲的宫廷中长大,但米蕊茉没多少机会跟男孩相处。约翰王的骑士大多已经过世,或者早就解甲归田,散居到爱克兰等地。尤其是祖父过世前几年,除了每天照顾老王饮食起居的仆人,整个宫廷空空荡荡。接下来,母亲去世,父亲一见她跟少数同龄伙伴在一起就会眉头紧锁。他自己懒得花时间陪女儿,却找了些讨人嫌的老头和老妇,把她关起来学习贵族的礼仪和责任,对她的一言一行吹毛求疵。而等到父亲当上国王,米蕊茉孤独的童年也基本宣告结束。
莱乐思,她的贴身侍女,几乎是她唯一的同伴。小姑娘崇拜米蕊茉,把公主的每句话都记在心上。相应地,她也会把跟哥哥姐姐一起经历过的事讲给她听——她出身于某个男爵家庭,是一大家子中最小的一个——公主听得入迷,尽量不对她家心生嫉妒,但她确实很想跟莱乐思换个位置。
因此到了瑟苏琢,莱乐思的样子才让她那么难过。记忆中那个活泼的小女孩不见了。一同逃出城堡之前,莱乐思有时是很安静,是会被很多事吓倒,可如今,女孩眼睛深处却像住了个全然不同的生物。葛萝伊声称在女孩身上发现了一些特质,米蕊茉努力回想之前有没有过类似的征兆,但除了莱乐思经常做些清晰、复杂,甚至骇人的梦,此外什么都想不起来。听着莱乐思的描述,那些梦如此详实,如此奇特,米蕊茉不禁怀疑是不是小姑娘自己瞎编的。
米蕊茉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的王位后,她发现自己虽然被人团团包围,同时却又孤独得可怕。海霍特的每个人都痴迷于毫无意义的权力,米蕊茉在其中生活了这么久,对此却没有半点兴趣。在她眼里,那就像一群坏孩子在玩莫名其妙的游戏。有几个年轻人向她大献殷勤——更确切地说,是向她父亲献媚,因为他们都把婚约看成带来财富和权力的手段——但在她看来,那些人就像行尸走肉,是披着年轻躯体的无聊老头,或是假装成熟的阴郁男孩罢了。
而在麦尔芒德和海霍特,唯一能享受生活却不浪费时间争权夺利的,便只有那些仆役。尤其在海霍特,比起阴郁的贵族,一批批女佣、男仆和小厮就像属于另一个种族。有一次,她心情悲痛地感到,偌大的城堡就像一片翻转的墓园,吱嘎作响的尸体在地面上行走,活人却在地下笑语欢歌。
西蒙等人就这样进入了她的视线——都是些别无所求,只想做自己的男孩。不像父亲臣下的贵族子弟,他们并不急着学习长辈那咔咔作响的步伐、喋喋不休的话语,以及絮絮叨叨的礼节。她看到他们在工作时闲晃,捂着嘴嘲笑彼此的蠢事,或在庭院草地上蒙眼捉弄别人。她渴望能融入他们。他们的日子似乎很简单——虽然稍微想想,她也知道仆人的生活劳累而艰辛,但她依然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像脱下斗篷般摆脱王家身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她从来不怕辛苦,唯独恐惧孤独。
“不对。”西蒙坚决地说,“你不该让我离你这么近。”
他稍微挪动脚步,转动手中的剑柄,用裹着布的剑刃将她顶开。转眼间,他又紧紧贴上她的身子。他的气息如此强烈,混杂了汗水、皮衣和上千片潮湿的碎叶子的味道。他的身材如此高大!她有时竟忘记了这一点。这突如其来的印象令米蕊茉的脑子停转了。
“你露出了空当,”他说,“如果我用上小刀,你就没命了。记住,你的敌人总会比你的攻击范围更远。”
她没收回自己的剑继续练,而是把它丢到地上,空出双手猛推一把西蒙的胸口。他踉跄后退几步,总算恢复了平衡。
“那就离我远点儿。”米蕊茉转身走开几步,弯腰捡起几根用来烧火的树枝,好让颤抖的双手有点事做。
“怎么了?”西蒙吓了一跳,“我伤到你了?”
“没,你没伤到我。”她抱起一把木柴,丢在他们清理出的林间空地上,“我只是暂时玩腻了这个游戏。”
西蒙摇摇头,坐了下来,解开缠在剑上的布条。
今天他们早早就扎了营,当时太阳还高挂在树梢。米蕊茉决定,明天他们就沿一直陪伴的小溪转道河川路——今天溪水的走向正是如此。河川路在伊姆翠喀河边,穿过斯坦郡,直入哈苏山谷。她解释说,他们最好等到午夜上河川路,这样在黎明前还能赶一段路,不然得在森林里待一整晚,外加一个白天,然后才能在夜间上路。
这几天来,除了清理灌木丛,她还是第一次用上真剑。是她率先提议,想在晚饭前练一个小时的——而她突然又说不练了,真让西蒙迷惑不已。米蕊茉左右为难,她想告诉西蒙这并非他的错,但又没来由地觉得这本来就是他的问题——谁叫他是个男人?谁叫他喜欢上了自己?谁叫他非得跟来?让她独自一人岂不是更好?
“别在意,西蒙。”最后她说,好像光是开口就耗尽了全身力气,“我只是累了。”
西蒙放松下来,将脏兮兮的布条小心地解开,团成一团丢进鞍囊,随后跟她一起坐在尚未点燃的火堆前。“我只是希望你小心点。我告诉过你,你的身子太靠前了。”
“我知道,西蒙。你确实告诉过我。”
“你不能让比你高大的人靠那么近。”
米蕊茉暗自希望他能停止这个话题。“我知道,西蒙。我只是累了。”
他似乎发现自己惹恼她了。“不过你很棒,米蕊茉,很厉害。”
她点点头,专心打火。一颗火星落入木屑,却没能将之成功点燃。米蕊茉皱了皱鼻子,又打一下。
“要不,我来试试?”
“不,不用你帮忙。”她又徒劳地敲了一下。她的胳膊都酸了。
西蒙看看木屑,又抬头看看米蕊茉的脸,迅速低下头去。“还记得宾拿比克的黄粉末吗?有了那个,他在暴风雨中都能生火。我们在司齐豁时,我见他用过一次,当时下着雪,刮着大风……”
“给你。”米蕊茉站起来,任由燧石和火镰滚落到木屑旁边的泥地上,“你来吧。”她走向自己的马,在鞍囊里翻找起来。
西蒙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还是专心地打起火。他打了好长一段时间,运气不比米蕊茉好多少。最后,等她用手帕捧了一包食物回来,他才终于打着一粒火星,生起了一蓬火焰。她站在他身边,发现他的红发已经很长了,打着卷儿垂在肩上。
他尴尬地抬头看着她,眼里满是对她的担心。“怎么了?”
她没理会他的问题。“你头发太长了。吃完饭我帮你理理。”她解开手帕,“这是最后两个苹果。不知怎么搞的,有点儿干了——鬼知道范巴德从哪儿弄来的。”她知道约书亚的补结来源,吃着吹牛大王范巴德的战利品,让她有种莫名的愉悦感。“还剩了点儿羊肉干,但也快吃光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得试着打猎了。”
西蒙张开嘴,但又合上了。他吐出一口气。“用树叶包住苹果,埋在火炭里。马倌舍姆经常这么干。这样就无所谓干不干了。”
“那就试试。”米蕊茉回答。
米蕊茉身子后仰,舔了舔手指。刚才她被热苹果烫到了指头,现在还有些隐隐作痛,但这点牺牲很值得。“马倌舍姆,”她说,“真是个聪明人。”
西蒙笑了,他的胡子上还粘着果汁。“味道不错吧。可惜已经吃光了。”
“反正今晚我也吃不下别的了。等到明天,我们就上路去斯坦郡,沿途肯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
西蒙耸耸肩。“不知道老舍姆现在在哪儿。”过了片刻,他说道。篝火爆裂飞溅,之前包着苹果的叶片被燎得焦黑。“还有鲁本、瑞秋。你觉得他们还在海霍特吗?”
“为什么不在?国王依然需要马夫和铁匠,宫里也缺不了女仆总管。”她冲他淡淡一笑。
西蒙咯咯笑了。“没错。我没法想象有人能把瑞秋赶走,除非她自愿离开。把豪猪拖出树洞都比这容易。就算是国王——我是说,你父亲——也别想撵走她。”
“坐好。”米蕊茉突然一阵手痒,“我刚才说过,得给你理理发。”
西蒙摸摸后脑勺。“你真觉得有这个必要?”
米蕊茉相当肯定。“绵羊每季也得剪一次毛嘛。”
她取出磨石,磨快了匕首。刀刃擦过石头的声响,活像火圈远处的蟋蟀唧唧鸣叫的响亮回音。
西蒙扭头看了一眼。“我感觉自己就像安东祭上的腌肉。”
“吃完腌肉,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啦,看前面,别说话。”她站在他身后,结果挡住了火光;她坐下,却又够不着他的头。“别动。”她说。
她拖过来一块大石头,在湿地上硬生生留下一条印记,坐在石头上,高度终于合适了。米蕊茉抓起西蒙的头发,审慎地查看。只割掉末端一部分?……不,还是多割点儿。
他的发质比看上去好些,虽然厚,但也柔软,不过因为这些天的旅行而搞得脏兮兮的。她皱起眉头,不知道自己的头发又乱成了什么样子。“你最后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她问他。
“什么?”他惊讶地问,“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你的头发里全是泥土和树枝。”
西蒙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每天在这该死的林子里钻来钻去,你觉得我能多干净?”
“行啦,这样子我可没法理。”她考虑了一下,“得先洗干净。”
“你疯了吗?我拿什么洗头发?”他自卫似的缩起肩膀,仿佛她要威胁捅他一刀似的。
“我说了,不然我没法理。”她站起来去拿水囊。
“那是喝的水。”西蒙抗议道。
“出发前我会灌满的。”她平静地说,“好了,头往后仰。”
她想了想,要不要先把水烧热?但她厌倦了他的抱怨,于是直接拎起水囊,浇在他头上,同时暗笑他气急败坏的咒骂。随后她拿起渥莎娃在奈格利蒙赠送的硬骨梳,不顾西蒙气恼的抗议,尽量把他的头发理顺。有些发丝缠得太紧,她就用指甲解开。这活儿没那么容易,她不自觉地越凑越近。湿发的味道加上西蒙刺鼻的体味,不知怎么还挺好闻的。米蕊茉不禁轻声哼唱起来。
她尽力梳好打结的头发,再度拿起小刀,开始修剪。正如她所料,光是切掉乱糟糟的发梢没法让她满意。为了防止西蒙再度抱怨,她加快速度,没过多久,他的后颈就露了出来,几个月没晒太阳的皮肤显得十分苍白。
她盯着西蒙的脖子,看着他宽阔的肩膀,看着向发际线延伸的越来越厚的金红色发丝,突然有了些感动。
人人都有些神奇之处,她朦胧地心想,人人都有。
她的指尖轻轻拂过西蒙的脖子。西蒙跳了起来。
“嘿!你在干吗?好痒。”
“呸,闭嘴。”她在他背后笑了,但没让他看到。
她继续修短他耳边的头发,只在开始长胡子的位置留下短短的发茬。她梳下他的刘海,同样切短,随后走到一旁观察,确保他的眼睛没被挡住。他的一绺白发如闪电般耀眼。
“这里就是被龙血溅上的地方?”在她的指尖下,白发和红发的触感没什么区别,“再跟我说说吧,那是什么感觉。”
西蒙似乎想说些玩笑话,但停了停,他却轻声说道:“跟……跟其他感觉都不一样,米蕊茉。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当时我很害怕,好像有人在我脑袋里吹响了号角,被溅到时就像火烧一样。我记不得太多了,直到我在山洞中醒来,看到了吉吕岐和黑斯坦。”他摇摇头,“当然不止如此。但有些事很难解释清楚。”
“我知道。”她任由湿漉漉的发丝从手中滑落,吸了口气,“理完了。”
西蒙抬起手,摸索着后脑勺和左右两边。“感觉短多了。”他说,“真希望能亲眼看看。”
“等到早上,对着溪水就能看到了。”她又笑了。傻傻的笑,毫无来由。“早知道你这么臭美,我真该带块镜子来。”
他转过脸,假装丢给她一个轻蔑的眼神,随即挺直了身子。“我有镜子啊。”他得意地说,“吉吕岐送我的!在我的口袋里。”
“我以为它很危险!”
“看看而已,不会的。”西蒙起身走到鞍囊旁边,起劲儿地东翻西找,像头在空树干里寻找蜂蜜的熊。“找到了。”他说,但又马上皱起眉头。他一只手拿着镜子,另一只手伸进鞍囊,继续摸索。
“怎么了?”
西蒙取下整只抽绳袋,拿到火边。他把希瑟窥镜递给米蕊茉,后者小心——甚至惊惶——地捧着它,他则在口袋里翻来翻去,心情越来越绝望。最后他停了下来,抬头看着她,双眼瞪圆,一脸失落。“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白翎箭。不在里面。”他从袋子里抽出双手,“安东宝血啊!肯定是落在了帐篷里。我当时肯定忘了放回去。”他的脸上又多了几分惊恐,“希望我没把它留在瑟苏琢!”
“你把它带回帐篷了,对吧?那天你想把它送给我。”
他慢慢点头。“没错。它肯定是在帐篷里。至少没丢。”他低头看着空空的双手,“可它不在这儿。”他大笑起来,“我想把它送出去,可我猜,它不喜欢这样。宾拿比克告诉我,这是希瑟的礼物,不要小看它们。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河上旅行吗?我把它拿出来炫耀,结果自己掉下了船。”
米蕊茉悲伤地笑了。“我记得。”
“我还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不是吗?”他叹了口气,满面愁容,“不过也没办法。如果宾拿比克找到了,他会好好保管的。我也不需要用它向吉吕岐证明什么——假设我还能见到他的话。”他耸耸肩,努力挤出笑容,“能把镜子给我吗?”
他举着它,小心查看自己的头发。“真好。”他说,“后面很短,就像约书亚他们。”他抬头看着她,“就像凯马瑞。”
“像个骑士。”
西蒙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过了会儿又拉起米蕊茉的手,用温暖的手心裹住她的手指。他没对上她的眼睛。“谢谢。你理得很帅气。”
她点点头。她很想抽出手,离得远一些,但又因他的碰触而感到高兴。“不用谢,西蒙。”
终于,他不情不愿地放开了她。“我想,如果要在午夜动身,那我们该睡了。”他说道。
“是该睡了。”她表示同意。
他们整理好不多的行李,在友好——也有些许不安——的沉默中打开了铺盖卷。
夜半时分,米蕊茉被惊醒时,嘴上捂着一只手。她想尖叫,但那手捂得更紧了。
“别叫!是我!”那只手抬了起来。
“西蒙?”她喘着气说,“你这白痴!你想干什么?”
“安静。附近有人。”
“什么?”米蕊茉坐了起来,徒劳地盯着黑暗,“你确定?”
“我快睡着时听到的。”他在她耳边说,“不是做梦。等完全清醒,我又听到一次。”
“是动物吧?一只鹿?”
西蒙的牙齿反射着月光。“我没听说有什么动物会自言自语,你呢?”
“什么?”
“安静!”他低声说,“你听。”
二人静静地坐着。米蕊茉只能听到自己的心怦怦狂跳,甚至盖过了其他响动。她朝篝火瞟了一眼。几块余烬还在发亮,这说明如果真有别人,他们已经彻底暴露。她心想,现在才熄灭火炭,是不是已经太迟了?
随后,她听到了。一阵清脆的噼啪声,似乎在百步开外。她的皮肤起了鸡皮疙瘩。西蒙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又是一声,这次似乎更远些。
“不管是什么,”她轻声说,“听起来走远了。”
“等几个小时再上路吧。我觉得没必要现在冒险。”
米蕊茉想反驳——说到底,这是她的旅行,她的计划——却无言以对。一想到月光之下,沿着蜿蜒河岸前行时,后面还跟着什么东西……“我同意。”她说,“我们等到天亮。”
“我会保持清醒,先守会儿夜。回头把你叫醒,我再休息吧。”西蒙盘着腿,背靠树桩坐好,剑横搁在两膝。“睡吧。”他似乎很紧张,又像在生气。
米蕊茉的心跳有所放缓。“你说它在自言自语?”
“嗯,也可能不止一人。”他说,“但听着不像有两个。我只听到一个声音。”
“它都说了什么?”
她能模糊地看到西蒙摇摇头。“我不知道。声音很轻。只是……几个词。”
米蕊茉躺回到铺盖上。“可能只是个猎人。也有人住在森林里的。”
“也许吧。”西蒙声音平淡。米蕊茉突然意识到,他这么说话是因为害怕。“林子里什么都可能出现。”他补充道。
她把头后仰,看着树冠间透出的几颗星星。“如果你困了,西蒙,千万别逞强。记得把我叫醒。”
“我会的。但我暂时不觉得困。”
我也是,她心想。
被人追踪的念头令她惴惴不安。如果跟来的是约书亚叔叔的手下,那他们为何一声不响地离开呢?如果是林中强盗,假设西蒙没被惊醒,他俩已经在睡梦中遇害了吧?或者那真是只动物,西蒙只是听错了?
米蕊茉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梦里,她看到一个头长鹿角、双足行走的身影在林荫中移动。
他们花了大半个上午才走出森林。伸展的树枝和缠脚的灌木像在拖拽他们。林地上升起的雾气过于浓厚,要不是有溪水声指引,米蕊茉相信他们早就迷路了。二人终于踏上湿淋淋的丘陵地时,已是浑身酸痛、大汗淋漓,衣衫比黎明时更加破烂。
他们在起伏的草地上骑行一阵,临近中午才抵达河川路。这里没有雪,但天色险恶而阴沉,森林浓雾似乎也尾随而来——所见之处全被大雾笼罩。
河川路空空荡荡,他俩这一路只遇见一辆牛车,上面载着一家人和他们的家当。车夫面容憔悴,实际年龄很可能比外表年轻,光是经过时朝西蒙和米蕊茉点点头,似乎就耗尽了他的全部力气。米蕊茉扭过头,看着瘦骨嶙峋的牛拉着车子向东缓缓而行。她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要去瑟苏琢,找约书亚碰碰运气。车夫及其消瘦的妻子,还有安静的孩子们,看上去都是那么悲哀、那么疲倦。想到他们可能要去一个已被遗弃的地方,令她很是心痛。米蕊茉很想提醒他们,王子已经挥师南下,但最后还是硬起心肠,转过头去。这么做太危险、太愚蠢:一旦与约书亚有关的消息传入爱克兰,会引来太多不必要的注意。
从中午到日暮,他们经过的几个小村似乎都已荒废,只有寥寥几间房子的烟洞里还能飘出比雾气稍浓些的灰烟,表明在这片阴郁的大地上依然有人生存。即使这里曾经有过耕地,现在也已看不出任何迹象:田里满是黑乎乎的荒草,却连一只牲畜都没有。米蕊茉猜测,如果整个爱克兰的状况都跟这里一样糟糕,那么,还没被吃掉的猪、牛、羊等牲口一定会被严加看管起来。
“我不确定我们该在这条路上走多久。”米蕊茉眯起眼睛,从宽阔泥泞的大路望向西方染红的天空。
“这一天只见到十几个人。”西蒙回答,“如果被跟踪了,我们最好待在开阔地,方便观察后面有没有人。”
“但我们很快就到斯坦郡的外围了。”米蕊茉随父亲来过几次斯坦郡,她很清楚目前的位置,“那个镇子比我们经过的小村庄大得多。路上会有行人的,肯定有。或许还有卫兵。”
西蒙耸耸肩。“也许吧。那我们怎么办,穿过野地?”
“我相信没人会注意到我们。你没看到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锁吗?天气太冷,人们不会往窗外看的。”
作为回答,西蒙喷出一口白雾,露出微笑。“听你的。只要小心别让马踩进泥塘。天快黑了。”
他们拨转马头,离开大路,穿过一丛稀疏的灌木。太阳几乎完全落山,地平线上只剩一抹淡淡的红光。风越吹越猛,抽打着长长的草叶。
当他们能看到斯坦郡时,夜幕已然降临至丘陵地。村镇覆盖了河道两边,中间有桥相连,北岸杂乱无章的房子几乎延伸到森林边缘。西蒙和米蕊茉在坡顶停下,俯视着闪烁的灯光。
“比以前小了。”米蕊茉说,“它曾经占据了整片河谷。”
西蒙眯起眼睛。“我觉得没变——看,一路过去全是房子,但只有一半有火光和灯光什么的。”他摘下手套,朝手指呵口气,“那么,我们今晚住哪儿?你身上有住店钱吗?”
“我们不住店。”
西蒙扬起眉毛。“不住?好吧,至少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顿热饭。”
米蕊茉转脸看着他。“你还没搞清楚,对吗?这是我父亲的领地,我曾经来过这里。就算没人认出我们,但路上行人这么少,所有人都会问东问西的。”她摇摇头,“我不能冒这个险。也许你可以去买些吃的——我确实带了点钱——但住旅店?那还不如雇个号手沿途通报呢。”
虽然在晦暗的光线下看不分明,但西蒙似乎脸红了,声音里也带上了明显的怒意。“你说了算。”
她压下脾气。“拜托,西蒙。你以为我不想把脸洗干净,坐在长凳上吃顿真正的晚餐吗?我只想更保险一些。”
西蒙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点点头。“对不起。你很明智,我只是有点儿失望。”
米蕊茉突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我知道。你是个好朋友。”
他猛抬起头,但什么也没说。二人一起骑下山坡,进入斯坦郡所在的河谷。
斯坦郡有些不对劲儿。大概六年前,米蕊茉来过这里,记得这是个热闹繁华的镇子,大多数居民是矿工及其家人,哪怕在夜里,窄街上也都灯火通明——但现在,即使有少数行人,他们似乎也只想赶紧回家。就连镇上的酒馆都像修道院一样安静,几乎空空如也。
米蕊茉等在“楔子与甲虫”酒馆外的阴影里。西蒙进去花了几个锌锑,买了些面包、牛奶和洋葱。
“我问店主有没有羊肉,他却死盯着我看。”西蒙说,“我想今年不太景气吧。”
“他有没有问你什么?”
“他想知道我打哪儿来。”西蒙已经啃起他的面包,“我说我是个蜡烛匠,从哈苏山谷来,想找份活儿干。他又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说:‘好吧,你已经发现这儿没啥工作了,对吧?’幸亏他没打算招人,杰瑞米教过我怎么做蜡烛,但我早就忘光了。他问我离开哈苏山谷多久了。他说那边山上闹鬼,还问我是不是真的。”
“闹鬼?”米蕊茉感觉后脊骨爬上一股寒意,“这话题真瘆人。你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我离开很久了,一直在南方旅行并找活儿干。不等他继续打听,我又说我老婆还在河川路的马车里等着我,然后就走了。”
“你老婆?”
西蒙咧嘴笑了。“是啊,我总得说点儿什么,对吧?不然大冷天的,一个男人买完吃的,干吗急着往回跑?”
米蕊茉轻蔑地哼了一声,爬上马鞍。“我们得找个地方休息,至少小睡一会儿。我累坏了。”
西蒙环顾四周。“不知道我们能去哪儿——就算没有烟雾和灯光,也很难分清哪些房子是空的。有的屋子没主人,但有的可能只是没柴火。”
就在他说话的当口,天上下起了小雨。
“我们得走远点儿。”她说,“镇子西郊应该能找到空谷仓或小屋。那边有个很大的采石场。”
“听着不错。”西蒙拿起一颗干瘪的洋葱,咬了一口,“你带路。”
“别把我的晚餐也吃光了。”她愠怒地说,“还有,别把牛奶弄洒。”
“不会的,我的小姐。”他回答。
二人沿涉林路——斯坦郡的一条主干道——向西骑行。米蕊茉似乎受到了西蒙的影响。确实,黑乎乎的屋子和店铺看不出有没有人,但她总觉得有人在里面偷窥,仿佛窗缝间藏着许多眼睛。
他们很快来到镇外的农场。雨势减弱,化成稀稀落落的毛毛雨。米蕊茉指指采石场的位置,从涉林路这边望去,那就像个巨大的黑洞。路面随山坡稍稍攀升,他们看到采石场的矮墙后闪烁着红色的火光。
“有人在那边生了火。”西蒙说,“一堆大火。”
“也许他们在挖石头。”米蕊茉回答,“但不管他们在干吗,我们都没必要知道。看到我们的人越少越好。”她离开大路,拐进一条小径,远离采石场,往河川路的方向走去。小径泥泞不堪,最终米蕊茉决定,点燃一支火把也比冒险摔断马腿强。于是他们下了马,西蒙尽量用斗篷挡住细雨,让米蕊茉设法打亮燧石。终于,她敲出一星火花,点燃了油布。
两人又往前骑行一小段,发现了避雨之处。那是间立在田里的大棚,周围长满野草和荆棘。棚主的住家显然在几百步外的峡谷里,看上去也已荒废,但米蕊茉和西蒙不敢确定那间房是不是真的空了,相较而言,还是棚子更安全些。它至少比露天更干燥、更舒服。于是他们把马拴在棚后一棵粗糙多瘤的苹果树上——很遗憾,树上没结果子——以避开下方镇中那些屋子的视线。
在火把的照耀下,他们看到棚内的泥地中间有堆潮湿的稻草,墙边则放了些缺胳膊少腿、等待修理的生锈工具。米蕊茉找到一把锈蚀的镰刀。见它被人遗忘,公主不禁有些心酸;但它表明这棚屋已被闲置很久,又让她十分欣慰。米蕊茉打消疑虑,同西蒙一起走出棚子,取下他们的鞍囊。
米蕊茉将稻草踢成两堆,把自己的铺盖放在其中一堆上。她挑剔地四下打量一番。“真想冒险生堆火。”她说,“但连火把都让我不放心。”
西蒙已将火把插进泥地,离稻草堆远远的。“吃饭时得有点儿光。”他说,“吃完我再把它灭掉。”
他们就着冷牛奶咽下干面包,风卷残云般吃完。等二人用袖子擦净手指和嘴唇,西蒙抬起头。
“明天怎么打算?”他问道。
“骑马赶路啊。如果天气还这样,我们没准得白天上路。不管怎样,到法尔郡之前,路上不会再经过其他镇子,也就不会再遇见什么人。”
“如果附近都跟斯坦郡一样,”西蒙说,“我们一整天确实见不到几个人。”
“也许吧。但要听到可疑的声响,比如有骑手接近,我们还是要离开大路,以防万一。”
米蕊茉喝下水囊里最后一口水,安静片刻,然后钻进自己的铺盖,盖上了斗篷。
“要不要跟我谈谈你的目的地?”西蒙终于问道。从声音里,她听得出西蒙是想问得谨慎些,以免触怒自己。他的慎重感动了她。但自己真是个暴躁易怒的孩子吗?这个念头又让她有些生气。
“我现在不想谈,西蒙。”她背过身子。米蕊茉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但也不愿透露心中的秘密。她听到他爬上铺盖,接着又轻声咒骂自己竟忘了熄灭火把。他爬了起来,穿过棚子。
“别弄湿了,”她说,“不然下次点火会比较麻烦。”
“说得太对了,我的小姐。”西蒙的声音酸溜溜的。只听咝的一声,火灭了。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他爬回铺盖的声音。
“晚安,西蒙。”
“晚安。”听起来他有些生气。
米蕊茉躺在黑暗中,思考着西蒙的问题。她应该向他解释吗?在所有人听来,她的理由都会显得很蠢,不是吗?她父亲挑起了这场战争——更准确地说,她相信是在派拉兹的挑唆之下——那她又该如何向西蒙解释,自己要去见他,要跟他谈谈呢?她知道,这理由不光是蠢,还像是最糟糕、最鲁莽的疯狂之举。
说不定真是这样,她阴郁地想。如果我是在自己骗自己呢?我可能会被派拉兹抓住,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然后又会发生什么?我知道多少约书亚的秘密,那个红袍怪物也会知道多少。
她开始发抖。为什么不能告诉西蒙自己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她没告诉约书亚叔叔,却要逃了出来?可她只告诉了他一点点,就已经让他又愤怒又怀疑了……也许他是对的。她是谁?不过是个年轻女子,又怎么能为约书亚叔叔及其追随者们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她现在的所作所为,算不算一时冲动,反将别人的性命攥在了自己手心呢?
但那并非一时冲动。她觉得自己被劈成了两半,就像她的父亲和叔叔,矛盾的双方,相互激战。这事很重要。除了我父亲,没人能阻止这一切,而只有我才知道这一切因何而起。可我真的很害怕……
想想自己曾经做过什么,自己又打算去做什么,她的心再也无法平静。她突然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除她以外,没人知道——没人!
她憋在心里的东西快蹦出来了。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空气。
“米蕊茉?米蕊茉,怎么了?”
她奋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应声。她听到西蒙靠近过来,稻草沙沙作响。
“你生病了,还是做噩梦了?”他的声音很近,几乎就在她耳边。
“没有。”她喘着气说,抽泣声却再也无法抑制。
西蒙用手推推她的肩膀,然后犹豫地碰了碰她的脸。
“你哭了!”他惊讶地说。
“嗯……”她拼命吐出完整的字眼,“我……我……我很孤独!我想回、回、回家!”她坐了起来,两手抱膝,将脸埋进潮湿的斗篷布中。又一阵汹涌的泪水淹没了她。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自己却站得远远的,鄙视地看着自己的分身泣不成声。
真是软弱,它恶狠狠地对自己说,难怪你总是求而不得。你太软弱了。
“……家?”西蒙疑惑地说,“你想回到约书亚他们身边?”
“不是,你这白痴!”她恼怒于自己的愚蠢,暂时压下啜泣,终于又能说话了,“我想回家!我想让一切都恢复原状!”
黑暗中,西蒙朝她伸出手,将她拉近。米蕊茉挣扎了一下,然后才将头靠在他的胸口。她很难受。“我会保护你。”他柔声说道,声音里带着奇怪的音调,一种平静的骄傲,“我会照顾你的,米蕊茉。”
她挣开他的怀抱。棚屋的门缝间漏出银色的月光,她能看到他乱糟糟的头发轮廓。“我不想被人保护!我不是个孩子了。我只想让事情都回到正轨。”
西蒙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久,随后,她再度感到他的手臂环住了自己的肩膀。她以为自己又快发火了,结果却听到他温柔的声音。
“对不起。”他说,“我也很害怕。对不起。”
听到这话的同时,她突然意识到身边的人是西蒙,而非自己的敌人。她控制不住地倒在他的胸口,一时只想渴求他的温暖和坚强。又一波泪水涌出她的眼眶。
“好啦,小米蕊。”他无助地说,“别哭了。”他伸出另一条手臂,紧紧抱住她。
过了一会儿,泪水平息下来。米蕊茉无力地靠在西蒙身上。她感觉他的手指抚过自己的下颌,抹过自己的泪痕。她靠得更紧了,像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用脸颊摩挲着他的脖子,感受着他皮肤下血液的脉动。
“哦,西蒙。”她声音沙哑,“对不起。”
“米蕊茉。”他唤了一声,随即陷入沉默。她感觉他的手向下滑去,温柔地托起自己的下巴。他把她的脸转向自己,转向他温暖的呼吸。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她在颤抖,在沉默,她知道他没出口的话语是什么。然后,她感到他的嘴唇挨上了自己的嘴唇,他的胡楂轻柔地蹭着她的嘴角。
一时间,米蕊茉好似脱离了真实的时间,漂浮在虚渺的彼岸。她想寻求一个藏身所、一个避难处,她想逃离风暴般紧缠自己不放的痛苦。他的嘴唇柔软而温柔,但抚摸她脸庞的手在颤抖。她也在颤抖。她想陷进他的身体,就像扎入一汪平静的池水。
一幅画面出现在她眼前,恍如梦境的片断,令她猝不及防:阿庇提斯侯爵趴在自己身上,一头浓密的金发在灯光下闪耀。拥抱的手臂突然变成了扣紧的爪子。
“不。”她猛地挣开,“不,西蒙,我不能。”
他飞快地松开手,像个被逮个正着的小偷。“我不是……”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平淡而冷酷,跟心中狂暴的感情旋涡一点儿也不搭,“我……我只是……”她一时失语了。
寂静中突然传来一个怪声。过了很长时间,米蕊茉才意识到声音来自棚外。他们的两匹马发出紧张的嘶鸣。紧接着,门后传来树枝的折断声。
“有人在外面!”她压低声音说道。之前的混乱心情消失了,冰冷的恐惧取而代之。
西蒙摸索着自己的剑。找到之后,他站起身挪到门边。米蕊茉跟在后面。
“要开门吗?”他问。
“我们不能被人抓住。”她严厉地耳语道,“不能被困在这里。”
西蒙犹豫了一下,朝外推开门。与此同时,门外一阵骚动,有人正急匆匆地逃走。透过雾蒙蒙的月光,只见一道影子正奔向大路。
西蒙踢开缠在腿上的斗篷,冲出棚屋,朝那逃跑的人影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