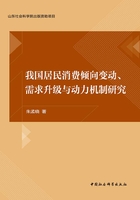
第三章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特征
第一节 消费倾向变化过程
本节主要是对居民消费倾向的总体变化进行考察,从而对居民消费倾向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并形成初步的判断。
一 消费倾向对居民消费需求的衡量
大量的文献都基于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现实状况对消费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来说,因观察视角的不同,对我国消费不足分析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也会不同,其中不少文献都采用消费率指标来判定居民消费支出的偏低性。同时,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变量是最为常用的两个不同层面的消费需求衡量指标。
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一个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指标,即用消费项目支出与收入之比来表示;另一个是消费率指标,即消费支出额占GDP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项)与GDP之比,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与GDP之比。最终消费率常被用来衡量总量经济中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协调关系。如果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保持固定的比例,那么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可以反映消费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情况;否则,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会有不同意义。我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有着各自不同的变化规律,那么,用消费率来衡量消费需求状况,两种消费率(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是不能被视为完全相同的。[1]消费率与平均消费倾向的计算区别在于选取指标的不同:前者是消费和GDP的比值;后者是消费和收入的比值。二者在经济含义上的区别是:消费率直接反映消费与投资(或积累)的总量关系,而不能直接反映居民相对于个人收入的消费支出状况,因为居民消费是以其可支配收入为前提的。于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更能直接体现居民相对于个人收入的消费支出状况。以往关于消费不足的大量研究,多是以消费率为主要参考标准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而忽视了消费率的经济含义,其结果是这些研究对居民消费需求的认识存在着偏差。由于居民消费是以收入而不是以GDP作为参考基准,所以以消费率为主要参考标准来衡量居民消费也就会有所偏差。因此,考察居民相对于个人收入的消费支出应该用反映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平均消费倾向来衡量。
表3-1表明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支出、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总体消费率和城乡居民消费率的变化状况[2]。从表中可以看出,居民总消费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其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下降到37.4%,之后2015年达到38%左右;而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大约为60%左右,即便是高储蓄率的东亚国家其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也大约是54%。钱纳里等人(198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当人均GDP为1000美元左右时,其对应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是76.5%和61.7%。但是,当1998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的时候,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46.5%,表现出和国际通行规律明显的不吻合性。同时,我国的内需一直不振,而偏低的消费率是我国扩大内需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的对比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城镇居民的消费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具有各自的变化特征,在2000年以前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方向: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而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基于对现实的观察,本书认为对于消费率的分析应当需要区别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而不能把这两者视为完全相同的两个部分。即在考察我国消费率的时候,不能从总体上混为一体,而应当考虑到不同主体的行为差异。
表3-1 我国居民消费情况

续表

续表

如果居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近似(相等),那么就可以通过对消费率的分析来推断消费倾向。考察居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之间是否存在近似(相等)的关系可以直观地发现,相对于较快的GDP增速而言,收入的增速是明显偏低的。那么,直接用消费率来推断消费倾向,以及使用消费率这一变量来研究居民消费行为是不严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分析居民消费的时候,就必须使用将收入和消费二者联系起来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一变量来考察居民消费。
二 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
我国经济发展既是一个快速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和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实际收入的不断提高必然会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调整,居民消费倾向作为衡量消费需求状况的主要变量也必将以我国的经济环境变化为背景呈现出相应的变化趋势和特征。
1.平均消费倾向
如表3-2和图3-1所示,城镇和农村的平均消费倾向具有阶段性特征。在1978—1989年之间,城镇平均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平均消费倾向,前者在稍低于90%处浮动,后者在85%处浮动;1989—1996年之间,农村和城镇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趋同以至相交,与前一阶段比较有下降趋势,并且中间农村平均消费倾向微弱超过城镇平均消费倾向;在1996—2007年之间,两者的平均消费倾向都降落到70%—80%区间,城镇平均消费倾向有较平稳的下降趋势,农村则有较大的波动:先下降又上升,先低于城镇又在2004—2005年超过城镇。近几年来,城镇平均消费倾向有一定的下降,而农村平均消费倾向有一定的上升。总的来看,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都有长期下降的趋势,而农村平均消费倾向表现出更大的起伏或波动。
表3-2 转型期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

续表


图3-1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的时间序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根据当年价格计算;图中指标由原始数据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计算得出。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袁志刚(1999)认为转轨时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结合收入对比趋势的特征,一个发现是农村平均消费倾向与农村城镇收入之比有较强的波动性(其相关系数并不大,但是收入对比滞后5期与农村平均消费倾向的相关系数约为0.857),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思考的问题是,这些波动之间是否反映了什么内在机制或规律,农村相对于城镇的收入波动与其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另外,虽然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平均来看,农村不及城镇收入的50%),但是两者的平均消费倾向却差别不大,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信息是,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倾向有持续的下降趋势,而相对来讲农村的消费倾向变动稳定性较差。
我们进一步考虑不同收入层次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过程。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对居民收入进行了分组,例如,城镇居民按照收入水平高低划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由于仅能获得很少年份的农村居民收入分组及其消费数据,所以这里我们只对城镇居民收入分组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进行考察。表3-3显示了城镇居民各个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总体来看,在考察期内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趋势不明显,其他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都有下降趋势,尤其是近几年下降较快。各年来看,较高收入水平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小于较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这说明居民收入差距因素会对消费倾向产生影响。但是,要研究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消费倾向的效应,还需要对居民收入分配现状进行细致地、可靠地分析。在本书中,只把收入分配因素作为消费倾向的一个基本解释变量,对消费倾向变化的收入分配因素不作深入的考察。收入水平过低者处于消费发展的低级阶段,很少考虑对于支出量级较高的新兴项目的消费,从而几乎不存在跨期替代的储蓄规划,其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且稳定。有两种情况使得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或者平均储蓄倾向较高:收入过高超过正常消费所需时会造成储蓄比重增加,这一般对应于收入水平较高阶层;为消费需求升级(包含预防性消费的要求)而进行的财富积累而带来的储蓄比重增加,这一般对应于中等收入水平阶层。前一种情况收入对消费需求升级的约束较小;后一种情况收入对消费需求升级的约束较大。
表3-3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

续表

2.边际消费倾向变化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MPCt是t时期居民边际消费倾向,△CONSUME是消费支出变动额,△INCOME是收入变动额。
经过测算,城乡居民各年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如表3-4、图3-2和图3-3所示。需要指出,这里的边际消费倾向为年度计算值,并不是回归拟合的结果,所以有的数值超出常规范围。但是这里主要考察边际消费倾向的趋势变化,其中的异常值并不影响分析。例如,经济的快速转型使得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波动,有几个年份的边际消费倾向计算值大于1,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中边际消费倾向处于0—1之间的假设并非一致;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存在统计上的缺陷等原因,其个别年份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负值。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各年边际消费倾向呈上下波动变化,但是总体变化趋势是下降的,近几年已下降到60%左右的水平。而农村居民的各年边际消费倾向波动起伏比较剧烈,其总体趋势也是下降的,但相对于城镇居民下降幅度较小,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经过70%左右的水平,相对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且近几年有所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处于0.90—0.97之间;2002年至2007年,美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0.86—1.31之间的较高水平。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MPC和美国相比显得很低,至少相差0.3,而且还具有跨时上的下滑变化趋势。
表3-4 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


图3-2 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图3-3 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三 消费倾向下降问题
进一步的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对居民消费需求倾向水平有一个基本判断。各种消费理论假说几无例外地将消费与收入联系起来。根据凯恩斯的消费需求理论,消费函数是C=α+βY,C和Y分别是消费和收入,β是边际消费倾向,那么平均消费倾向C/Y=α/Y+β。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指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的提高而递减。直观的理解是:贫穷的人其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而富有的人其收入用于消费的份额降低。据此,则消费倾向与收入变化是负相关的。但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在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假设下以及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可能更倾向于增加储蓄,因为他也许只能通过储蓄积累的方式来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凯恩斯的理论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它无法解释所谓的“消费之谜”,即富人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小于穷人。同时,根据莫迪利阿尼等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续收入假说,人们会根据其一生的效用最大化来规划自己的消费计划,平滑其一生消费,并最终完全耗尽他们的财富,消费和收入基本呈正比,即消费倾向基本不变。对于一个给定的收入增长率,长时间内收入和财富是成比例的,储蓄、消费和财富随时间成比例增长,这就是著名的储蓄率长期恒定的结论(安格斯·迪顿,2005)。
对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需要判断消费倾向下降是否正常,或者下降的程度是否正常。本书认为,作为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的过程,我国居民消费应具有强劲的增速加快势头,供给的发展会为消费需求创造更大的选择空间,收入增长与消费需求升级应该具有一致性。另外,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幅下降,目前占比低于40%,这个比例大大低于大多数国家,在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排名最后,也低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的个人消费占比为55%;韩国的个人消费占比为48%;美国和英国的个人消费占比分别为71%和67%。[3]我们没有获得国外居民消费倾向数据,无法进行国际比较而具体地对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水平进行判断,但考虑到振兴居民消费的目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和提高居民个人消费(消费倾向)虽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后者是消费者基于可支配收入的消费决策问题),但在扩大内需、振兴消费的宏观实现上是一致的。同时,根据对居民消费倾向下滑变化趋势的分析和考察,本书认同已有研究对我国消费不振的判断,我国居民消费比重的持续走低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分析需要密切结合当前居民的消费需求变化,深入探讨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以及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