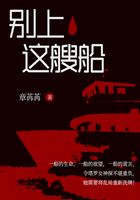
第15章 赤海(8)
艾丽丝其实不叫艾丽丝,十年前,在尖沙咀的酒楼里卖唱的时候,一个男人端着一杯酒,唤她过来,然后问:“靓女,叫什么名?”
艾丽丝摇摇头。
男人道:“没有名?那以后可怎么点你的曲?”
艾丽丝脆生生地回答:“你唤一声‘妹仔’,我便过来了。”
“你个子细成这样,要不是听到在唱《碌碌碌》,都看不见你个人。”
艾丽丝歪了歪头,这个男人让她有一些奇妙的身体反应,脸上烫烫的,心里酥酥的;大师爸跟她讲过,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靓仔,都要懂得面冷心更冷的道理,才不会乱了方寸,从前她不明白其中道理。反正每个酒楼,日场连宵夜,要摆上百桌,每桌流水一般的客,哪一个都见识过。面孔浓油赤酱的码头工、一身烧鹅味的古惑仔、点一碟花生米并一壶烧酒便坐上大半日的白发翁、眼睛色眯眯的烂赌鬼……出手最阔绰的还是那些江湖大佬,见她娇小可爱,便常唤过来,要她唱《客途秋恨》,然后给她一张“红衫鱼”(百元面值钞票)。
大师爸唤艾丽丝作“妹仔”,一叫她便应,已习惯了;倘若当天赶了三个酒楼,拿回去的钱多一些,还能赏她一张“青蟹”(十元面值钞票),至今为止,她每天都把枕头包里的青蟹点算一通,已存了足足一百零三张。
眼前的男人,与烂赌鬼、绅士客都有些不同,他眉眼压得低,下巴削得尖,耳畔两块青头皮干干净净,沾了一些茶渍的白礼帽就放在手边;看她的表情里,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反正并不像能给她驼背佬的,但是肯定也不会掏出青蟹,她闻到他身上微微的酸气,大师爸讲过,那叫“穷酸气”。
“总不能永远叫你妹仔吧?”他笑了,鼻翼两侧的纹路很精致,这让她觉得特别受用,比起每次穿街走巷时碰上的少年烂仔,他要漂亮得多。
“先生要点什么曲?”她努力保持“面冷心更冷”。
“点个你不会的。”
“我没有不会的。”
他眉毛微微抬了一抬:“《摇咕橹》,会不会?”
她笑了,退后一步,抬头挺胸,唱道:“摇咕橹,草个新心抱,心抱几时归?年年后日归。有乜约归?又有仪龙硬饼共生鸡。阿婆唔食得生鸡骨,哽得阿婆硬吉一,猪仔又争,狗仔又争,争崩阿婆果个米仔甖。阿婆走出门边哭,阿公过海买猪蹄。买得猪蹄煲苡米,人人食碗去担泥。担起泥归甕芋仔,芋仔出芽心抱归。”
这一曲,唱得地动山摇,博得满堂彩。
“妹仔,你唱得好,可惜我没有钱给,点算?”他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
她内心涌起一股怒气,但还是努力压抑住了,这样的白吃客,从前不是没有对付过。
“一张青蟹都没有?”她问。
他摇摇头:“没有。”
“那等一歇,表哥会过来跟你要。”
根本没有什么“表哥”,但她不这样编,今天就要做白工了。
“这样吧,你让表哥不要过来,我送你一件好东西,要不要?”
“什么好东西?”
男子的声音糯糯的,带一些甜气:“送你个名。”
“我不要名,我要钱。”
“有了名,钱会来得更快,以后人人记得你的名,便能多点你的曲。中不中意?”
她到底年纪小,心里有气终要发泄出来,便鼓着腮帮子道:“那你给我取什么名?如果我不中意,你还是要付钱。”
“叫元宝,好不好?你嗓子靓,人更靓,跟金元宝一样惹人爱,大家唤你的时候,都能沾沾财气,未来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像是在逗她。
她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以后,我只要一唤你,你就过来唱给我听,不收钱,可不可以?你那个表哥,让我来当。”
“那我要叫你什么?你都是表哥了,我不能不知道我表哥的名。”
“我姓原,原百烈,你叫我百烈便可以了。”
“连这点钱都赖,像个女的,哪里烈了?无如叫小凤算了。”她脆生生回击他。
“那也好,你爱叫我什么,便叫。”
他彻底把她最后一层防卫拆掉了,就这样,她从今往后都成了“元宝”,尖沙咀各大酒肆里的“招财女”,大家“元宝、元宝”地叫,她便穿来跑去,满场飞。更吊诡的是,也是从那天起,她到哪里,小凤便跟到哪里,坐在某个角落,静静听她唱;这间酒楼唱完,她转场,他便跟住她,带她穿过那些阴暗的街巷,有油脂仔上前骚扰,他便一声不响地出手,把他们的牙齿打落。
那些日子,让艾丽丝意识到,她终于成了小凤袋里的一只大“元宝”,所谓“落袋为安”,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安稳,快快乐乐地待在一个男人的“袋子”里。
小凤与元宝的组合,很快便在酒楼里出了名,艾丽丝每晚在收场的时候,总要走到他跟前,为他唱一曲,作为当日的终结。小凤都是笑嘻嘻地听完,便站起来,戴上白礼帽,双手插袋,跟在她后头,走出酒楼。
也是很久以后,艾丽丝才从大师爸口中得知,小凤就是他派来给她当“表哥”的。她盯着大师爸,半晌没有讲话,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动气。可是那以后,连着好几天,她都不跟小凤说话,也不为他唱收工曲。
小凤像是知她的心意,也不招惹她,但是非常坚持地护送她转场、归返。某一天,她终于忍不住,回身狠狠抽了他一耳光,流着眼泪道:“如果你不是大师爸的马仔,还会不会这样跟着我?”
“会。”小凤讲。
这才让艾丽丝放了心,终于又跟他讲话了,就这样相伴整四年,她长到十六岁,来了初潮,于是暗地里下了决心,先把身体给小凤,再任凭大师爸去摆布,以后无论她身边出现什么男人,都忍得下来。可是做女人的事情,哪里瞒得过大师爸的眼,老头子只盯了她一眼,便道:“跟你讲过,做女人一定要面冷心更冷,靓仔无心,说了多少遍?你听得进去么?你听不进去,便去打听打听,原小凤是什么样的人。”
艾丽丝这才得知,小凤早有一个情人,系石塘咀的红牌阿姑,他付不起艾丽丝的卖唱钱,却都投给了那个阿姑。艾丽丝气极了,不顾酸胀的小腹,以别扭的姿势走到他跟前,对他讲:“你说要一直这样跟着我的,这个话当不当真?”
“妹仔啊……”小凤摸一摸她的头,这一摸,便让她恍惚又回到了十二岁,“你终究会遇上好靓仔的。”
她愣在那里,听见整个天地崩坏的声音,格外刺耳。
次日,小凤便不见了,听闻是卷了大师爸一笔钱,便逃掉了。大师爸带着人气冲冲赶去石塘咀的花寨,要找那阿姑,结果老鸨跟他讲,那阿姑前一晚上吊自尽了,奇怪的是,脖颈上有两道勒痕。
末了,老鸨还阴恻恻地说:“老契把钞票给阿姑,阿姑却把钞票去给更靓的靓仔,这就是因果循环,终要有报应的啦。”
小凤这一走便是整三年,三年间,艾丽丝的胸脯鼓胀了,腰肢更细了,屁股变得又圆又厚,穿个旗袍,就跟没穿一样,曲线毕露。这期间,诸多双眼睛都瞄准了艾丽丝,她心里清楚得很,早晚落到这些人手里,于是把心一横,便主动跟大师爸讲:“你给我找一个男人吧,谁都可以,好手好脚便可以。”
大师爸笑起来,抽了两口烟,跟她讲:“难得你想得明白,那就找一个。”
找来的男人,是大师爸的一个契弟,虎背熊腰的,常年在赌场跑,替大师爸收保护费,要比小凤整整高出一个头,人也更年轻些。艾丽丝自小便厌烦这个人,他口太花,动不动去拍她的屁股,从十二岁被拍到十八岁;好几次,她都想跟小凤去告状,叫他也打落他那满口黄牙,可转念一想,还是罢了,小凤跟他去拼命,不见得能占上风,万一他被打坏了,她这一世都不能原谅自己。
就这样,大师爸摆了一场酒,也算是正式把艾丽丝给了这个契弟。艾丽丝这一次可算是真正的“面冷心更冷”,她早已准备好一根桐木筷,要给自己破身,这样,便没有谁更对不起谁。
那一晚,是契弟带着艾丽丝穿过夜巷,要领她到自己的住宅,他手里还提着一瓶壮阳酒,系从大师爸那里拿来的。她心脏怦怦跳得很快,好几次都想转身逃走,可是右手腕被对方擒得紧紧的。走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前头有辆自行车,唰一下撞过来,冲开了艾丽丝与契弟,她还未回过神来,便看到那契弟倒在马路中间,双手捂住头,嗷嗷直叫。
她想走上前看看他,又不敢,因为根本爬不起来。
“傻女!走啦!”
煞车皮的声音“嗞”一记钻进她的耳膜,把她激醒了;那个熟悉的声音,那只温热的手,鼻翼两侧柔软的纹路,又扑向了她,将她的命运重写。
她坐上自行车后座,两只手死死勒住他的腰,她对自己发誓,此生此世,都不会放开他。
就这样,原小凤把艾丽丝的人生定格在了那个凶险而烂漫的夜晚,他握住她肥沃的双乳,让自己一点一点挤进她的身体,嘴唇贴在她耳边,跟她讲:“你是我的元宝,你要记得,一世都记得!再忍一忍,还要来,还要来……”
她又痛苦又兴奋,觉得老天爷应该就此让她死掉,因为往后的日子,她不敢想。
翌日,艾丽丝睁着彻夜未合的一对眼,看着原小凤起身的背影,他套上绸衬衫,然后门便被撞开了,两个壮汉扑进来,将原小凤一把摁在地板上,她的脸皮被粗糙的水泥磨出了血。她只能拼命捂住嘴,不让眼泪掉出来。
“小凤,你就是不肯让人省心。”大师爸走进来,将椅背上的旗袍拎起,丢在艾丽丝赤裸的身体上,“两条路,一、你们一道去见阎王;二、跟我做一些大事。自己选咯,不过要快,我年纪大了,没什么耐性。”
艾丽丝并不畏惧大师爸,她怕的是小凤,因看到他眼睛里的光黯淡下来了,这是要妥协的征兆,她太清楚他了,从一根手指的曲度,就能猜到他的最终决定。
那以后,小凤便又离开艾丽丝,又是离开了整三年。
三年之后再回来,她看着他,已是心如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