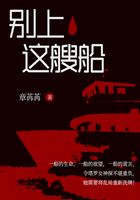
第6章 起航(5)
杜春晓真当对艾丽丝充满了兴趣,兴趣大到出航头一晚,便混到一等舱的宴客厅去看她的表演。所谓的“宴客厅”,不过是一个不到六十平方米的公共舱,腐蚀的木壁板草草刷了一层米色的漆,地毯上的破洞被木头凳脚压起来了,吊顶灯不晓得是哪个旧仓库里翻出来的,水晶挂坠上斑斑点点看得极清楚,灯光一打,照得厅内似被泼墨。红酒味、雪茄味、刨花水味、头油味、雪花霜味,甚至还有一点猪屎味,掺在一起,倒是与现场相得益彰。宾客也少得可怜,只稀稀拉拉坐了五六桌,都是懒洋洋的,操着广东话的阔太们神情冷淡,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子穿得西装毕挺,站在桌前跟她们推销一种装在瓶子里的口红;他熟练地旋开盖子,将滴管里的猩红汁液涂抹在手背上,趁色香味没有散尽之前,迅速伸到阔太的鼻尖底下:“埃及人就是这么样弄的,要装瓶,才能保鲜……闻一闻,红玫瑰香气的,红玫瑰颜色的,男人碰到要发狂的。”阔太们微微张了张眼皮,也不搭话。
三五个侍者也是不大动的,站在那里,手里执一个盘子,盘上摆的酒杯上还有口红印。
一组五人乐队坐在台面上,一根单簧管,一根长笛,一把大提琴,一架鼓,一台钢琴,乐师穿着皱巴巴的白色礼服,打紫红色领结,钢琴手打了个哈欠,抖了抖肩膀。
像五条狗。
杜春晓心里想。
“像五条狗吧,上面那帮乐师。”凤爷点了点台上。
她不敢猜测他是怎么会有完全一样的想法,只能坐下来,啜了一口红酒。
逃亡生涯让她基本上已经忘记穿好行头是什么样的感觉,但今天这一身,还是让杜春晓没丢面子。古绿色宽身旗袍,背上织染的银色凤头已经抽丝了,只得用杏黄的丝绸围巾披盖住;头发紧紧地扎盘起来,把脸皮拉得光溜溜的,口脂抹了三四遍,这样便省去了敷面的花粉。即便如此,她的落魄相依旧显而易见,之所以没有在进厅的时候被阻拦,全仰仗凤爷抛出了一个大洋的小费。
“看来,今天艾丽丝是不必表演了。”她咂摸出了廉价红酒的味道,不是涩味,也不是酸味,是掺了水的、让人会发火的味道。
琴师“嗞”的一声,在弦上拉出长长的滑音,刺耳极了。
但是底下的人并没有抱怨,反而是下意识地坐正了身体,打算看接下来的表演。只有凤爷,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剪掉了一个雪茄头。他的坦然令杜春晓很诧异,一个通缉犯竟也明目张胆到这种境界?转念一想,又觉得正常,他若不是那么样招摇,恐怕更像个逃犯。
灯光暗下的那一刻,杜春晓直觉气氛完全没变,卖口红的男子不说话了,但仍然举着那只红艳艳的手背,坐到角落的一张椅子里。阔太们把红酒杯推到一边,低头交谈几句,微光打在脸上,竟是很复杂的表情——期待中有一点儿不耐烦。
一段流畅的钢琴乐音把杜春晓的百无聊赖击碎了,她倒是未曾想到,这钢琴师手艺竟然挺高明,这种弹奏水准,她只在上海滩的一个高级夜总会里见识过,也是爵士乐,甚至演绎的竟是《暗刀麦奇之谋杀叙事曲》。
这首曲子的前奏,听得最入迷的当数凤爷,因那差不多就是他自己的故事。眼部的朱砂记被昏暗洗褪了,那个辰光他堪称是标准美男子,可以放到电影里去跟胡蝶配情侣档的那种美。
舞台中央一束灯光落下,艾丽丝就站在那里,穿一身红丝绒跌膊连身长裙,浓卷发上扎了一根直冲天际的红羽毛,在半空飘啊飘的,说不出来的好笑。
咦,不是男人的歌吗?怎么要女人来唱?
杜春晓正纳闷呢,艾丽丝一开腔,她便懂了。那老沉嗓子,像是油里泡过的,结了厚厚的包浆音,闷闷的,又哑哑的,胸口包着一个硬核一般,想吐又吐不出来,就这样奇迹般地拥有了一副精致烟嗓。杜春晓也听得出来,艾丽丝的英文唱白是听上几百次唱片模仿出来的,但是也似模似样,每个吐字都在拍子上了。当日当时,她选了这样的曲子,大抵是要唱给杜春晓一个人听的,杜春晓明白,侧脸瞟了一下凤爷,他的手指居然还在膝盖上打拍子。
“什么时候来啊?”坐在杜春晓前头一桌的阔太终于扭头问旁边的侍者,那侍者尴尬地弯下腰,把阔太的空杯斟满。
“急不得的,这一急,他(她)更不来了,人家什么都知道。”另一位阔太这样劝道。
“哪个人要来?大明星么?”
杜春晓怎么都想不到,凤爷居然探身到两位阔太中间,笑嘻嘻打探起来。那块朱砂记并没有折损他的俊俏,所以阔太们刚把眼睛斜过去,表情便软下来了。
“没听说么?神仙要来。”性急一些的阔太脱口而出。
“哎呀,不要乱扣名字。”另一位阔太掩着嘴巴,冲凤爷嫣然一笑,“是古婆婆咯。”
“古婆婆?”凤爷将脸更凑近了她们一些,“哪个古婆婆?”
性急的阔太又急起来:“古婆婆都不知道?可是个大神通哟。”
凤爷刚想继续问,一曲已终,灯光复又亮起来了,他的朱砂记暴露在两位阔太眼前,她们脸上的娇笑片刻凝结;他明白,是该抽身离开了。
杜春晓环顾四周,嘴唇愈扬愈起,一首歌的工夫,下面竟不小心人满为患了。最远处一张桌子边,竟坐着几个穿白色船员服的人,最显眼的那位手边摆了一顶大盖帽,五十岁左右,面膛黑黑的,皱纹从眼角一直连接到嘴角,更像是僵固的肌肉线条;这种钢铁似的面孔,是专门长在领袖人物身上的,比如这位,任何人都看得出应是福和号上负责本次航行的船长。船长左侧坐着一位周身散发火气的船员装男子,不停往喉咙里灌啤酒,头发剃得接近全光,露出一点青色的发茬儿;右侧的船员要生得相对细巧一些,垂着眼,长睫毛微微盖住了眼珠,拿余光瞟着台上正在谢幕的艾丽丝,粗短的手指频频抠着杯沿。
刚刚那个口红贩子身边,也多出一个人来,雪茄抽得嗞嗞作响,烟雾缓缓绕住他鼓胀的肚皮;这个人看起来处境相当不错,挤进肥肉里的一双小眼睛看谁都是笑眯眯的;活得富贵的人,看什么都顺眼。
“哎呀,看来是要等那个什么古婆婆出场了。”凤爷拍了拍手。
两位阔太转过头,瞪了他一眼,凤爷还以一记骚气十足的口哨。
“你这要是在上海滩做个拆白党,也挺好呀。”杜春晓忍不住要奚落他。
“一点儿也不好。”凤爷突然严肃起来,直勾勾瞪着走下台的艾丽丝,“我最恨这种人。”
杜春晓笑了一下,没有再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限,哪怕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暴之徒。她是打心底里有一些喜欢凤爷,又特别怕他;他令她想起史蒂芬,世上唯一一个能让她遍体鳞伤的男人。
宴厅门再度开启,进来一行人,其中有三位是杜春晓熟悉的——梁玉棠、李孟存和佩嫂;至于那不认得的,竟系个大美人儿,鹅蛋脸形,眼睛细细弯弯的,嘴唇上没有搽口红,显得分外清爽,那一身蜜色和服也特别出众,金红相间的腰间垂下一个蓝色织锦钱包。
“哎呀,今晚真是赶上大热闹了哟。”凤爷的脸凑近了杜春晓。
这四个扎眼的人物一出现,全场便骚动起来,两个阔太的声音太尖,几乎所有人都听得到她们在讲:“咦?不是古婆婆?”
梁玉棠瘸着一条腿,一起一伏地走到两位阔太桌前,下巴抬得高高的。
李孟存挤出一脸尴尬笑容,道:“能不能请两位……”
“滚!”
梁玉棠只吐出一个字,掐断了仅存的友好气氛。
性急的阔太自然不服,冷笑道:“凭什么?”
“滚!”
梁玉棠再度出声。
一名侍者急匆匆上前,俯下身,在阔太耳边叨了几句,阔太面露惊恐,急忙起身,拉着另一名阔太往旁边去了。
侍者以最快速度收拾掉桌上的杯盘,扯掉桌布;另一名侍者亦快步上前,盖上干净的桌布,摆上干果盘与三杯红酒,这一系列动作的完成,花了不到半分钟。
梁玉棠选了最正中的位置坐下,李孟存与那日本美女坐在两旁,佩嫂仍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喂,靠边去一点。”凤爷抬手,轻轻推了一下佩嫂的背,“挡着本大爷了。”
佩嫂冷着脸转过头去,与凤爷四目交集,怔了半秒钟,便挪了一下位置。
凤爷这一系列的表现,也让杜春晓满心欢喜,就是这样快意恩仇,人生才有意思。
此刻,船长已带着两名船员登台,他熟练地微微屈身,对着刚刚被艾丽丝用过的话筒,道:“各位,欢迎登上福和号,来享受这一次的旅行。鄙人是负责本次航程的船长鲁运持。”
底下无人有反应。
鲁运持显然对这样的冷遇早有预料,便指着身边那位周身火气的船员道:“这位是我的大副杨威。”又指向另一侧略带羞涩表情的船员,“这位是二副李志森。往后的十天,就由我们来为大家服务,希望这次旅程能带给大家愉快的回忆。一路顺风!”
鲁运持举起红酒杯,底下的人愣了半晌,没有一个有动作。
“一路顺风!”高喊的是那位刚才一直在欢欢喜喜抽雪茄的大胖男子。
“一路顺风!”
众人这才有了反应,勉勉强强地举起杯。
鲁运持将酒一饮而尽,三个人走下了台。
杜春晓下意识地摸出一张高塔牌,放在桌上,冲着牌发笑。
“怎么了呢?这么想玩牌?”凤爷单手托腮,看着她手下压着的高塔牌。
“没什么,”杜春晓收起了牌,“我同大家一样,等着见那位古婆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