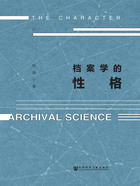
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关于“中国档案学”
本书所说的中国档案学是研究中国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学问,中国档案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古代,统治阶级颁布的档案管理规章制度中就蕴含大量的档案管理思想,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等思想;到了近代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运动”,文书档案改革进行得有声有色,再加上史学界整理明清档案的活动,我国出现了总结和探讨档案整理与利用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中国档案学正式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专门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系进行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确立,中国档案学迅猛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较大成绩,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之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中国档案学受到了一些“左”的思想的干扰,一度陷入消亡的境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档案学在宽松的环境之下重新繁荣和发展起来。
到目前为止,中国档案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档案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应用理论研究以及档案应用技术研究三大部分。其中档案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档案事业史、档案学史、档案法学、比较档案学、档案术语学等门类,档案应用理论研究包括文书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门类,档案应用技术研究包括档案计算机与网络管理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技术研究、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研究等。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面临各种挑战和困惑,既有信息技术革命、经济社会变革的外来挑战,也有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困惑,学科体系面临更新难题,理论层次面临突破瓶颈,未来中国档案学发展何去何从,是所有档案学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二 关于“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
所谓性格,是指某人对事物的稳定态度以及在其基础上成为习惯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性格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主体对客体的态度体系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16],性格是人格的核心,是一个人独特之处的主要代表,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人性格研究组将性格分为五个模块,包括生活旨趣、情绪特征、认知风格、态度倾向、意志品质,然后又将每一个模块进一步划分为若干性格特质,比如生活旨趣模块包括实惠性、奉献性、知识性、支配性四个特质,认知风格模块包括强烈性、激活性、持续性三个特质等,其中每个特质都有正反两极,在正反两极之间可以进行渐进的过渡,于是各种相互关联的性格特质经过一定的组织,就构成了一个性格网络,从而使人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17]。
一个人性格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遗传、体型、性别、社会文化、职业、子女教养等,但总体来说,性格是一个人内在心理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深度整合的产物。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注重“机体的整体性以及机体与其周围外界环境之协律性”[18],认为性格是指那些先天的倾向、意向与那些生活期间受生活印象的影响所养成的东西之间的混合物。可见,性格是在外部环境与人自身心理活动相互作用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形成是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人的性格与人的生理基础有一定的关系,但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关系更大,“社会环境对性格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19]。
关于政治性格,学界的观点不一,丁旭光认为,政治性格是一个人“从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中最为稳定的心理特征”[20];桑兵认为,政治性格是“通过政治姿态表现出来的个性因素”[21];罗伯特·莱恩认为,政治性格是“一个人面对外部政治刺激时所经常表现出的持久的、动态的反应”[22];曹传清认为,“一个人在政治活动中经常表现出的特有心理和行为就构成了他的政治性格,政治性格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23]。
综上可以看出,政治性格一般用于指称“人”,指一个人对待政治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这是学界较多采用的一种用法。但学界对于政治性格还有另一种用法,即用政治性格来指称“物”,比如学科、思想、期刊等,这是一种对于物的“人化”用法。比如邵宇的《论汉初儒学政治性格的基本转变》[24]讲的是儒学的政治性格的转变,他认为,汉初儒生通过对儒学进行法家化的改造,“援法入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并提出“三纲”“德主刑辅”的思想,实现了政治性格的转变,从而完成了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契合,并实现了儒学的制度化;潘希武的《自由教育的政治性格》[25]讲的是自由教育思想的政治性格,认为不能片面强调教育自由,而应该重视自由教育的政治性格,教育改革当中应该注意这种性格的影响;吴俊的《〈人民文学〉的政治性格和“文学政治”策略》[26]讲的是一本期刊的政治性格,认为《人民文学》的性格是多重的,但在这些性格当中最显著的性格就是政治性格。
本书的研究主题——“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所称“政治性格”即采用后一种用法,它是对中国档案学学科个性的一种人化描述,指的是中国档案学在主体态度、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环境等方面表现出的政治行政倾向和特色,比如中国档案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研究主体的政治行政认同、资政取向,研究对象的权力建构,研究环境的政治熏染等。
档案学界较早就提出档案学的政治性问题。那么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与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有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谈档案学的政治性不得不提档案工作的政治性,学界普遍认为,档案学的政治性来自档案工作的政治性,档案工作的政治性主要是指档案工作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主要体现在档案工作的服务对象、开放度以及机要性三个方面[27]。坚持档案学政治性的代表人物是吴宝康,他认为档案学具有党性,档案学的党性就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其论证依据为:首先,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基本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都是有党性和阶级性的,因此档案学也具有阶级性和党性;其次,档案工作在阶级社会中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档案工作就具有了阶级性,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阶级性导致了档案学的阶级性[28]。
档案学的政治性格与政治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联系在于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与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都与政治存在密切关联。但是两者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两者的观察视角不同。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是从一种人化性格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档案学的学科个性和面貌,它涉及中国档案学科内部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档案学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角色结构、研究对象、研究环境等。因此,其研究视角更加细致和全面。而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仅仅指的是档案学的党性、阶级性及其所要求的机要性,是从狭隘的阶级视角对档案学的探讨,很少涉及对档案学内部理论体系与政治行政关联的细致探讨。第二,两者的内涵不同。档案学政治性的内涵较为单一,单纯指的是档案学的阶级性;而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的内涵则更为广泛,包含了中国档案学发展中更丰富的政治行政内涵和关联,注重探讨中国档案学研究所表现出的政治行政特色,比如研究主体的政治行政认同、资政取向、(行政)实践方法,研究对象的权力建构,研究环境的政治熏染,中国档案学科未来发展走向等。探讨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有助于厘清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内在机理,属于学科元理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