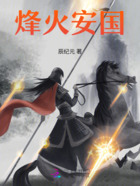
第18章 朝堂风云
信使历经数日奔波抵达京城。顾不上一路的疲惫,直奔朝堂而去。此时的朝堂上,大臣们正为北狄之事争论不休。
传信太监在殿外,高声喊道:“启禀陛下,边境陆逸将军有紧急信件呈上!”
皇帝坐在龙椅上,神色凝重,微微抬手:“呈上来。”
传信太监快步上前,从信使手中接过信件,呈到皇帝面前。皇帝打开信件,仔细阅读,脸上的神情愈发严肃。
他将信件递下给一旁的大臣传阅,说道:“陆逸在信中提出,边境局势危急,北狄大军压境,他手下有个叫冯沐芊的将士提议主动出击,诸位爱卿对此有何看法?”
此言一出,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
一位身着华丽朝服的官员站了出来,此人与陆逸有些宿怨,他微微眯眼,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狠,故意歪曲陆逸的出兵请求:“陛下,陆逸此举实在莽撞!他竟然听信一个无名小卒的提议,妄图进攻北狄。这岂不是拿我大梁的安危开玩笑?主动进攻,必定损耗大量兵力物力,若是战败,后果不堪设想!依臣看,陆逸这是居心叵测,想借此机会谋取私利!”
朝堂上一片哗然。一些官员随声附和:“李侍郎所言极是,主动出击太过冒险,万万不可!”
一位主张保守防御的老臣张太师缓缓站出,轻抚胡须,慢悠悠地说道:“陛下,老臣以为,主动进攻风险太大。我大梁军队向来以防御为主,坚守边境,虽不能彻底击退北狄,但也能保一时安宁。若是贸然出击,一旦失败,北狄定会长驱直入,我大梁百姓又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老臣为官数十载,见过太多因战争失利而导致的悲剧,实在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皇帝微微皱眉,没有说话,目光在朝堂上扫视一圈,似乎在等待着不同的声音。
一名年轻的武将赵义廷站了出来。抱拳行礼,大声说道:“陛下,臣以为李侍郎和张太师所言差矣!陆将军久经沙场,他的判断必定有其道理。如今北狄屡屡进犯,我们若总是被动防御,只会让他们愈发嚣张。
至于这位冯沐芊,虽只是个小卒,但她的提议或许是个转机。主动出击,虽有风险,但也有机遇。我们可以先派小股精锐部队试探,摸清北狄的虚实,再伺机而动。如此一来,既能打击北狄的气焰,又能为我大梁争取主动。臣愿领军前往边境与陆将军一同出征,为陛下分忧!”
皇帝听着大臣们的争论,心中犹豫不决。他看着争吵的众人,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试图从他们的表情和言辞中找到最正确的决策。这一决策关乎大梁的生死存亡,容不得半点差错。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丞相站了出来。丞相年过半百,面容和蔼,眼神中却透着睿智。他不急于表明观点,先是静静地观察着朝堂上众人的反应,从李侍郎的歪曲言辞中,他看出了其与陆逸的宿怨以及背后的私心;从张太师的话语里,也理解这位老臣对战争风险的担忧和保守防御的立场;而赵将军的热血豪情,也让他看到了年轻将领渴望建功立业的决心。
丞相微微躬身,不紧不慢地说道:“陛下,老臣以为,此刻急于争论主动出击或保守防御并无益处。陆将军的信件和诸位爱卿的争论都值得深思。主动出击和保守防御各有利弊,我们不能只看眼前,更要谋划长远。”他微微停顿,目光扫过朝堂,确保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
“如今北狄来势汹汹,我们确实不能坐以待毙。但在行动之前,需先稳住局势。加强防御是当务之急,不可有丝毫懈怠,这是保障百姓安全、稳定军心的基础。”丞相条理清晰地分析着,话语中透着沉稳。
“同时,收集情报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在边境增设哨岗,安排经验丰富的探子乔装深入北狄境内。但这些探子不能单打独斗,需建立一套严密的联络体系,确保情报及时、准确地传递回来。”丞相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仿佛在勾勒整个情报网的架构。
“再者,对于进攻,我们不能盲目行动。可以先从内部着手,挑选一批忠诚且有谋略的将领,让他们在军中秘密演练各种战术,针对北狄的特点制定应对之策。这样,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我们便能迅速行动,一击即中。”丞相的每一个建议都切中要害,既考虑到了当前的困境,又为未来的行动做好了铺垫。
皇帝听着丞相的话,微微点头,陷入沉思。朝堂上暂时安静下来,众人都在思考丞相所言。丞相这种不偏不倚、全面考虑的处事方式,让大家不得不佩服他的睿智。
在这紧张的氛围中,皇帝终于开口:“丞相所言甚合朕意。先加强边境防御,不可有丝毫懈怠。同时,派人密切关注北狄动向,收集情报。至于进攻一事,待朕与诸位爱卿商议出万全之策后,再做定夺。陆逸那边,先让他做好防御准备,不得擅自行动。”
正当赵义廷一脸无奈之时,皇帝扫视一圈朝堂,目光落在赵又廷身上,神色凝重又带着几分期许:“赵将军,朕命你即刻率领三万精兵、五千骑兵奔赴边境,与陆逸会合。此去边境,加强防御是首要任务,不可让北狄有可乘之机。同时,务必谨慎收集北狄情报,为日后进攻做足准备。你可有信心完成使命?”
赵义廷闻言,精神一振,“唰”地单膝跪地,胸膛高高挺起,眼神中满是坚定:“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定将北狄动向探查清楚,与陆将军一同守护好大梁边境!”
皇帝微微颔首,眼中闪过一丝欣慰:“好,朕相信你。此次任务艰巨,你需事事小心。若遇到难题,可与陆逸共同商议,切不可莽撞行事。”
赵义廷重重地点头,“臣明白!”说罢,他站起身,大步迈出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