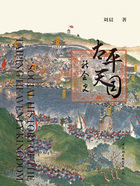
小引
咸丰三年(1853)春天,太平军金田起义的号角,从贫瘠荒芜的紫荆山,一路传入秀水江南,二月初十日(3月19日)攻克南京。随即,为拱卫京都,保障供给,太平天国决定回师西征,开辟上游基地,“陷一城即守一城,破一镇复收一镇”;[1]同时着手建立地方政权,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载:“初贼所破州县,皆掳其财物,残其人民而去,未尝设官据守。自窃占江宁,分兵攻陷各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伪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2]这就意味着太平天国开始面临地方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建设问题,而由于太平军对城市的军事化占领,大量人口向乡村地区流动,加之兵燹天灾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态和民生问题成为太平天国社会战略成败的重要考验。
据常熟碑刻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物《报恩牌坊碑》之序记载,太平天国治下的常昭地区(清时,常熟、昭文二县合城而治,统称“常昭”)的确是一片民殷财阜、年丰人乐的盛世景象:“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蝦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3]长期以来,这件实物成为褒赞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重要依据,有不少学者据此认定碑序是普通百姓感怀太平天国“轻徭薄赋”政略的真实流露。祁龙威在《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中,首先质疑碑序所记内容的真实性。他认为,“报恩牌坊”是“钱桂仁为首的一群叛徒们别有用心地谀颂忠王的作品”。[4]
这件实物的确没有忠实地展现普通民众的情感。首先,报恩牌坊不是百姓自发建造的事实已在多种时人日记、笔记中得到确证。龚又村《自怡日记》“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记:“舣舟至城……见报恩坊新造在丰乐桥堍,是匪党及乡官为伪忠王而建。”[5]陆筠《海角续编》载:“(同治元年)二月,贼慷天福钱桂仁将王市严氏节孝坊拆到南门外丰乐桥,改造报恩坊,以媚伪忠王李贼。”[6]曾含章《避难记略》载:“贼将王市严姓节孝坊拆去,改造于南门外丰乐桥东堍大街上,曰报恩坊,谓报忠王之伪恩也。”[7]三种史料均系当时人亲见亲闻之记载,可证报恩坊建造的发起者是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其缘起为地方官员谄媚忠王。因此,报恩牌坊虽系民间出资营造,可能摊派金额也不算大,但不是百姓自发而为。
其次,报恩牌坊的建造实际成为百姓的一项经济负担。龚又村《自怡日记》“同治元年三月廿七日”记:“定议筑海塘,造牌坊,修塘路及上忙条银每亩征钱七百廿,佃农疲惫不堪。”[8]造牌坊的费用系自民间征派捐税而来。据12种记太平天国时期常昭地区情况的主要史料,两年多的太平天国统治期,钱漕正赋外,常熟的苛捐杂税达28种。[9]以捐纳各项杂税之总额,“佃农疲惫不堪”的描述符合实际。
再者,在碑序描述的盛世景象背后,同样是在常熟,却发现了另外一种与之形成尖锐对立的历史场景:
旬日之间,郭外之北,由西至东,四方农人,闻风相应,各处效尤,打死伪官,拆馆烧屋,昼夜烟火不绝,喊声淆乱。闻长毛来往不绝,市廛罢歇,阛阓阒寂,良民东迁西避。各处坐卡长毛,回城请剿。起事乡村,以致又遭贼兵焚掠。[10]
“民变”遍及太平天国治下江南各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在“激变四野”的复杂态势下,太平天国与民众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形成对立。这种对立关系的产生、发展,值得回顾和省思,或许可以从历史遗存表面获取不一样的、更为真实的信息传达。
[1] 《钦差大臣向荣奏报攻剿上方桥续获胜仗折》(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档》第1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09页。
[2]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109页。
[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另参照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太平天国报恩牌坊碑序》拓本。
[4] 祁龙威:《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第3版。
[5] 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95页。
[6] 陆筠:《海角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9页。
[7] 曾含章:《避难记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8] 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98页。
[9] 12种史料为:《自怡日记》《避难记略》《鳅闻日记》《庚申(甲)避难日记》《海角续编》《漏网喁鱼集》《劫余杂录》《海虞贼乱志》《常熟记变始末》《守虞日记》《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汝南一家言》。28种杂税为:门牌费、役费、田捐、红粉钱、天王捐、支应费、难民捐、万民伞费、盐捐、礼捐、田凭费、海塘捐、免冲钱、学宫费、派捐、进贡钱、房捐、特捐、局费、上忙公费、执照费、船凭费、造牌坊捐、修塘路捐、经造费、剃头凭费、军需捐、行人通过费。
[10] 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