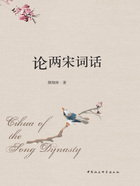
第三节 艳丽与道德——对于传统美学观念的纠偏
词是音乐与文学融合的艺术形式,出于按曲歌唱的需要,作词必须“倚声”。随着隋唐“燕乐”的出现,词始得萌芽。词是隋唐以来配合新兴之乐而填写的一种歌词。唐五代至宋初,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士大夫认为词之功能在于“用资羽盖之欢”和“娱宾遣兴”。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新唐书·温大雅传附温庭筠传》谓温庭筠“多作侧词艳曲”。词甚至被文人视为“艳科”或“薄技”。在传统文化观念或诗学意识中,词不具备“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0]、“征圣”“宗经”“文以载道”“经国之大业”等其他文体所具备的社会功能,被定位于“艳科”与“小道”的“词”,由于其“艳丽”的特征,就与“道德”存在一个精神的鸿沟。吴处厚对于上述艺术观念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为词的“艳丽”作了辩解,初步建立了一种新的词学观念。《青箱杂记》对“正人端士作艳丽词”作了如下的辩解: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乖崖张公咏席上赠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抟百花,抟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熏衣香入骨。维阳软縠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若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司马温公亦尝作《阮郎归》小词曰:“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11]
伯固对于词的“艳丽”非但不回避,反倒为之辩解。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消解传统艺术观念片面强调诗歌的认识功能和道德功能的做法,另一方面调和传统美学有关“艳丽”与“道德”的形而上学的矛盾对立,确立一种辩证分析的美学眼光。以现代的眼光考量,吴处厚词话体现出形式美感的主体性确立,纯粹的道德理念已经被社会生活的审美丰富性所消解,人需要感性的审美享受和艳丽化的文学写作,而词这种文体形式恰恰提供了这种写作的契机。
综观吴处厚词话,不乏吉光片羽、真知灼见,为“词话”这种批评样式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其局限性在于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没有建立较完整的词学概念或美学概念,不过作为前期的词学,其开拓意义是值得赞赏与称道的。
[1] (宋)李清照:《词论》。
[2] (明)孟称舜:《古今词统序》。
[3]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81页。
[4] 邓子勉编:《宋金元词话全编》(上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1页。
[5] [英]贝尔:《艺术》,周金环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0页。
[6]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7]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避暑录话》,田松青、徐时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127页。
[8] 缪钺、[加]叶嘉莹:《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96页。
[9] (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第1版,第5页。
[10] 《毛诗序》。
[11] (宋)吴处厚、何薳:《青箱杂记 春渚纪闻》,尚成、钟振振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