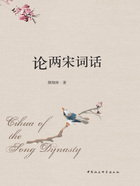
二 两宋词话的发展过程
1.词话之酝酿
两宋词话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词话的酝酿期、词话的发展期、词话的丰富期,这既是一种时间划分也是一种逻辑划分。笔者将整个北宋词话称为“词话的酝酿”时期,将南宋词话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和后期。前期与后期的时间分界线则大致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而这两个时间段,笔者又将之分别视为“词话的发展”和“词话的丰富”两个逻辑环节。
北宋词话处于萌芽时期,数量有限,且掺杂在其他文献之中,专门性质的词话著作不多,理论上所达到的水准也相对有限。然而,作为词话的逻辑起点,这一时期的词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包含了后来词话探讨的诸多艺术问题的思维胚芽,为以后词话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文献资料的原因,笔者选择了吴处厚词话、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李之仪词话、陈师道词话、赵令畤词话、魏泰词话、叶梦得词话这七个具有代表性的词话进行研究,就某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吴处厚的词话主要限于对北宋时期的词家进行观照,注重现象的描述,如对“药名词”这种词作形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汉语言的诗性特征去思考问题,从修辞理论上寻找艺术特性的解答。重要的是,吴处厚提出了“气象”这一美学概念,从艺术创作实践上进行论述,使理论与实践达到较好统一。对于词的艳丽与道德的关系,他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探讨,以辩证的态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词话这一批评方式初步有了理论分析的观念。
吴处厚的词话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尚未对词进行专门的理论探讨,因为它是由后人从他的文集中辑录而来,并且也不属于系统性的词的研究。相对而言,杨绘的词话则是对词进行专门性的研究,显露了自身的系统性。所以,《时贤本事曲子集》被认为是“词话的先河”,梁启超认为它是“最古之词话”。客观地讲,《时贤本事曲子集》在理论形态上并无多大的创见,它的潜在意义在于,它作为词话这种批评样式的逻辑起点,建立了特有的文体批评形式,这无疑是个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时贤本事曲子集》提出词的“本事”的美学特性,并以此作为对词的批评依据之一,为词之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梁启超评《时贤本事曲子集》:“纪北宋中叶词林掌故”,“据所存佚文,知其每条于本事之下,具录原曲全文,是实最古之宋词总集,远在端伯、花庵、草窗诸选本以前。且 述掌故,亦可称为最古之词话,尤可宝贵”。
述掌故,亦可称为最古之词话,尤可宝贵”。
李之仪词话,首先从修辞角度认为长短句于“遣词”最为“难工”,词的文字表达和象征比其他文学形式更为困难。其次,认为词自有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审美风格,有着“格”这样严格的形式规定,倘若背离它的艺术原则,就可能丧失美感。再次,认为词的音律之美超越了以往的诗歌,必须给予“胜韵”足够的重视。最后,在美学意义上,指出词的创作要“才”“情”兼备,尤其是“卒章”最好“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李之仪论词以《花间集》作为审美标准,其眼光主要眷注于其形式美,从文体特性考量词的艺术价值,开启了李易安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先河。在李之仪看来,和诗相比,词更适合摹写现实人生和表达生命的真切体验,可以淋漓尽致地抒写自我的生命欲望和审美情绪。
李之仪推崇贺铸才情俱佳,他从贺铸的生命态度和创作实践的关联上阐述自己的词学审美观。词和现实人生密切联系,是生活化的艺术形式,或者说它更贴近世俗化的欲望生存。如果说,诗之文体所表现的是情感闪烁普遍性的道德伦理色彩,那么,词表现的情感则更沉醉于个体的感性冲动和本能的欲望,私密性更强于诗,所以词的“本事”色彩要浓厚于诗,而“本事”多和红粉艳情相关。在创作上,李之仪赞赏才情俱佳的作品,强调审美的独创性。李之仪对于词的认识既从文体意义又从主体情致这两个密切联系的逻辑环节上来思考,认为词的文体特性适合表达生活情感,尤其擅长摹写两性之间的欲望冲动,当然这种欲望冲动形诸词的形式中而达到审美升华的效果。
陈师道对词话也有所涉及,他承袭杨绘的“本事”观念,认为词的创作多来源于现实中的种种机缘,强调词与创作主体的实践意志的密切关系。在理论上的创见是,提出“本色”的概念,为词的艺术特性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尽管有关“本色”的内涵尚缺乏严格的规定性,但毕竟展开了有意义的思维抽象的实践。
在赵令畤的视野中,词成为士大夫获得诗意栖居的新型精神工具,它体现出生命智慧和世俗享乐的双重品格,使主体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态度对待事物。无论是月夜赏花、酌酒助兴,还是调笑红粉、履历记游,都离不开词的出场。和诗往往承载厚重的社会历史的意识形态结构,表现深沉的道德理念和普世的情感忧虑不同,词是个人化的话语流露,属于私密化的生活享乐和审美超越的艺术形式,适合抒写个体性的欲望情绪,它的娱乐功能被作为主要的写作目标。因此,词和士大夫的诗意栖居的人生方式形成密切的精神应和。虽然赵令畤词话没有从纯粹理论的视界进行词的叙事功能的细致表述,然而,却从艺术实践上为词的叙事功能的拓展确立了典范,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因此,赵令畤词话所具有的美学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魏泰的“本事”词话不一定是“信史”,但也没有充足证据说其为虚构。魏泰词话揭示出官场文人因词结怨的状况,其中隐含的意义超越了讨论词的艺术价值问题,尤其值得今天的文人深思。魏泰具有那个时代可贵的超越性别偏见的豁达胸怀,赞赏女性所显示的写作天才,揭示了因为历史语境的变化,女人也能从事诗词创作并且显示令人瞩目的灵感的历史事实。
叶梦得对词的“本事”特征显然有更广泛的认识,意识到词这种文体更多涉及现实生活,直接抒写国事、政事、家事的内容。词更适合于表达个体生命的现实境遇和寄托超越苦闷的情怀。叶梦得把词看作超越苦闷的艺术工具,强调词所潜藏的心理慰藉的力量,认为词能鲜活地表现生命或生活的故事,它既来源于现实又抗衡现实的美学功能是十分强大的。叶梦得词话还对一些重要的词家进行评价,其评价融入了知人论世和知事论人的意识,运用了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但是,这种历史主义的评价着眼点依然是揭示词人词作的艺术价值和显明其审美的风格。
总的来说,北宋时期的词话一方面还不够丰富,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显得贫乏,但其意义在于,建立了批评的新文体和新方法,也初步形成了理论的胚芽,为后来的词话发展奠定了基础。
2.词话之发展
南宋前期词话,以杨湜的《古今词话》、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王灼的《碧鸡漫志》、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张邦基词话、袁文词话、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明清词话、王楙词话、洪迈词话、曾季狸词话、张侃的《拙轩词话》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词话在数量上比北宋词话有所增加,理论上也超越了北宋时期的词话,达到一个新的思维境界。
杨湜的《古今词话》论述词的生活内容的扩大,强调词与人生价值的密切关系,艺术视野进一步开阔,对于词的多种功能与特性有了深入的认识。他认为词对实践人生意义有重要作用,词成为达到一定精神品位的文化工具,这一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杨湜的《古今词话》还关注到词的审美功能的丰富,人生趣味与词的创作的密切联系,并相应作出理论阐释。它更突出的理论价值在于,在阐释学意义上对词家词作进行富有创见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有一些合理性的想象再创,对作家作品赋予新的意义,但也有一些不合理的主观猜测,远离文本的客观意义,不免有所失误。杨湜的《古今词话》,给我们留下了阐释学的正反两方面启发和教训。
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首创词选和词话合成的体例,论词喜爱采用汉儒解经的方法,以阐发道德观念为目的,提供了一种观念与方法相统一的词话意识。由于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散失较多,笔者只能就其所存篇目作简略的评价。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对节令和词的关系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对词的题材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民俗与词的艺术表现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词应该蕴藏民俗之美。不足之处是,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像杨湜的《古今词话》一样,也是机械地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对词作进行比附性解释,难免穿凿附会。这两个词话,均初步尝试逻辑分析的方法,将阐释学的观念运用到词家词作的研究中,呈现出开创性的意义。
王灼的《碧鸡漫志》共分五卷。卷一论乐,总述上古迄今的声歌递变的缘由,为词寻找艺术本体论的理论根据;卷二论词,历论唐季五代至南渡初期的词;卷三、四、五,专论词调。这部著作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词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表明了词话这种批评样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碧鸡漫志》涉及词的起源论和艺术本体论,从哲学的宇宙生成论和主客体相分的二元论来看文艺问题,所以站在一个较高的思维起点上。它提出词的审美标准——性情、自然、中正、雅等,并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入具体的探讨,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上为词的创作与鉴赏确立了自我的美学观念。《碧鸡漫志》对两宋词家的审美风格探讨较多,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开创了词话中审美风格论的先河。在批评方法论方面,运用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批评方法,同时还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显示了作者具有深刻的理论眼光和对方法论运用的重视。《碧鸡漫志》也是两宋最早和较完备讨论曲调起源演变的著作,它考证诸多曲调源流,阐释其音乐演变过程,“始创词调溯源之学”,使词话的有关曲调音律的研究升格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将美学焦点置放在词的艺术创作和批评鉴赏方面,更多讨论文学本身的因素,将以往词话关注的外部研究转向到内部研究,更多地思索艺术性和审美性的问题,体现了理论思维的初步成熟。尤其在词的创作方面,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如词的整体美和结构美、形式美和意境美等。在批评方面,力倡道德批评方法,并在具体的批评中予以实践,其次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以求实的批评态度进行词家词作的考证、评说,纠正以往词话的某些失误。并且,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将辩证分析和审美感悟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使词话这种批评样式达到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张邦基词话,肯定无意识在词的欣赏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梦幻对于想象力的激发和灵感、情绪的诞生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认为,词,也是抒写主体情境对生活场景的感受之作,它有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张邦基以客观陈述的方式表达出对词的创作的美学理解,认为词是主体情境的果实,而主体情境来源于世俗生活的客观场景,它们构成一个密切关联的精神因果,从而形成一个审美创造的艺术逻辑。
袁文词话偏爱对词的写作背景、动机、目的、作者等方面进行考证,力求揭示它们的真实客观性,以利于对词作的深入把握。袁文在对文本的批评过程中,流露出浓重的道德气味,而忽略审美的艺术批评。但是,对于某些文本的具体修辞技巧的分析,却显示出独到的领悟。袁文词话,在考据方面有所创见,在审美感受和艺术判断方面,则缺乏独到发现。
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善于对词作进行话语和意境的溯源,寻找其文藻修辞的依据。在考证基础上,既指出某些词作对前人的语词情境的仿袭,揭示出文本点化他人意境而有创新的审美特征。《能改斋漫录》以隐蔽出场的方式对词家名作进行艺术价值和审美特性的判断和评价。在批评风格上,它不同于机械僵化的“学理批评”,也有别于浮光掠影的印象批评,而是建立在对文本深入领悟之上的诗意批评,是将文本的审美直观和细致分析相结合而获得的艺术感受,因此能够传神地揭示出作品的美学内涵。吴曾词话,表明一种有别于西方美学的审美情趣和生命智慧,它肯定感官享受和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的密切关系,没有舍弃生命快感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而认为它们和美感存在着潜在或必然的关系,肯定生命存在的权力和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尤其意识到,女性的生命本体给予文人墨客丰富的灵感和才情的启迪,激发起审美的冲动和诗意的创造,词这种艺术形式更适宜表现对于女性美的审美渴望和忧郁情怀。《能改斋漫录》关注到词所寄寓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这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死亡意识。《能改斋漫录》对于词的题材丰富和趣味给予一定程度的注意,除了理论上有建树之外,精湛的考据也是其特点之一。
王明清词话反驳词为“小道”“末技”的偏颇观念,以现实生活的政治事件、政治矛盾和词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词也具有作为政治工具的意识形态功能。王明清认为,词的写作起源于有意识的政治倾向和鲜明的社会历史道德准则、主体世界的明确良知。另外,词与梦幻之微妙关系已有人论述,王明清以生动形象的故事和逼真传神的体验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问题。
王楙词话闪烁着论辩的色彩,不拘前人名家之成见,而以自我的思考和分析,纠正以往的偏见和谬误,从而获得独到的艺术见解,表现出可贵的思想独立。王楙博学深思,擅长考据的学术风格在词话方面也得到一定的体现。他喜欢从词语典故的溯源上寻找出词对于以往诗歌话语的取法与点化,澄清相关的某些对词作的误解和偏颇的观点,以获得客观正确的认识,揭示出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话语继承。
洪迈的《夷坚志》继承古人的“志怪”艺术传统,将它扩展到词话的领域。洪迈的《夷坚志》和《容斋随笔》对于词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丰富功能予以昭示,尤其注意到词的文体形式密切联系世俗生活、日常情境的特点,呈现它具有的人生游戏、生活智慧、机智幽默的审美趣味。洪迈对于词的艺术价值比较关注,能够从词作者的身份和个性考察词作的艺术风格,强调“情致”作为衡量词的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尺。洪迈注意探究词的话语修辞,认为炼词造句构成词的艺术价值的另一个体现。洪迈对于词的功能范围的认识显然有了拓展,尤其是意识到词广泛地写实人生和昭示命运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后一种功能的感受,流露出一种神秘主义的唯心论倾向,然而这种唯心主义的美学倾向也反映出一些有趣的艺术现象。
曾季狸对于词点化于诗及其他文体这一方面比较眷注,认为“夺胎换骨”才是“点化”的关键,一味模仿则丧失艺术的创新机能。因此,他对诸家的名作名句进行词语的考证寻源。曾季狸以简要评点呈现词人或词作的风格、气韵、意象、蕴含、神色、价值等方面,提出“思致”作为衡量词作的价值核心和审美标准,显然在理论中获得一个思维基点,相对而言,比一般仅仅专注于本事、考证、修辞等方面的词话略胜一筹。所谓“思致”,强调词作的精神意蕴,垂青于词的独特的审美境界和审美意象的营造,赞赏其呈现出某些富于超越性的生命智慧和想象力。因此,“思致”作为一个判断词作的美学标准,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词话概念被提升到理论的范畴。
张侃的《拙轩词话》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词的起源论有所丰富,二是在批评中广泛运用了词家词作的比较方法,树立横向与纵向的审美比较的典范。张侃的词之起源论,首先,透射着追本溯源的历史意识,显示其宏大的历史主义眼光,从文化产生的本源来思考精神生产的对象;其次,着眼于从艺术本体论的意义来阐释艺术形式的诞生,指出词来源于民间流传的口头歌谣,是人类文明的古老结晶;最后,从道德伦理角度,对词的变异提出批评,维护传统的宗经征圣、淳化民风的文学观念。《拙轩词话》在研究意识上树立了审美比较的原则,既注重从美学视界来比较不同时代词家的历史影响,又注意到同时代词作的不同的审美风格,具有历史与现实纵横联系的辩证思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深入地比较分析了词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审美要素,作出一些甚为精辟的结论。
3.词话之丰富
与以往词话相比,南宋的后期词话,一方面是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是理论水准的进一步提高。代表性的词话有岳珂词话、张端义词话、魏庆之词话、黄升的《中兴词话》、俞文豹词话、罗大经词话、刘克庄词话、陈郁词话、周密的《浩然斋词话》、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刘壎词话、张炎的《词源》等。
岳珂词话拘泥于现象的评点,理论建树不多。但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对刘过的名作《沁园春》的批评,揭示刘过词作的“白日梦”的创作方法,从而阐述艺术的梦幻美特性,对词作与潜意识的审美关系作出了思考。二是批评辛弃疾的词多“用事”,对词的艺术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岳珂词话主要是针对辛词“用事”的负面影响而言的,应该说岳珂论词目光敏锐而专注,善于发现问题,也较早指出辛词多“用事”的不足一面。岳珂词话与早期词话不同的特色之一是,在“词话”的叙述过程中,巧妙运用“对话”方式,且融入了戏剧化的情境、场景、气氛、表情、动作等因素,使词话这种批评方式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
张端义词话有意识地将作家和作品进行相统一的论述,并且能够在具体论述之中提出词学的概念和理论,达到具体和抽象的结合。传统的美学批评包含一定的伦理批评的色彩,一是因为传统的美学观念和道德观念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二是审美活动有时的确难以和意志活动划清界限。因此,伦理批评作为文艺批评的构成之一,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张端义词话,体现出伦理批评的倾向,甚至有超越审美的道德批判的倾向。词在两宋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或者说,作为一种流行的话语样式而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公共领域的普遍话题,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共享工具。如果说,上古时代,“不学诗,无以言”,那么在两宋,对词缺乏理解和掌握,就无法进入公共空间和进行对话、交往活动。所以,词的功能远远超越了诗的功能,尤其它渗透着世俗生活的交往和娱乐的功能,成为文化的公共领域。张端义词话对此有所感受和阐发。
魏庆之词话将主观批评和客观批评结合起来,在批评观念上,更辩证一些,获得了一些对词的艺术特性的审美发现,揭示出部分词人的艺术创作的独创性和审美风格的特殊性。应该说,其批评意识表明了南宋词话在批评意识上的自觉与不断完善。然而,魏庆之词话主要引述他人之见,自我创见不多。
黄升的《中兴词话》对词的看法,具有历史主义的思想意识,从历史背景及相关的文化语境来思考词家词作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较多从历史理性的视角去考察作品,如对胡铨、张仲宗等人的词作的分析就贯穿了上述意识。其次,《中兴词话》善于进行审美心理分析,从创作主体与文本符号的结合上分析词作的审美构成,既揭示词家艺术创作的心理隐秘,又对词的审美鉴赏心理进行解释。
俞文豹词话注意微观的文本分析,这种微观的文本分析建立于对词的话语解读,通过解读而阐释自己领会的意义。俞文豹对词的鉴赏,以直接明了的印象式批评和经验性批评贯穿始终,却能切中要害,指出其艺术价值的高下,时常有独到见解。对于词乐起源问题,尤其词与音乐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遥远而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往往又是根基性问题,它更能反映出思考者的历史观和文化意识以及艺术观和审美观。俞文豹词话也进行一些研究,通过对词乐的历史溯源,寄寓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罗大经词话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批评观念方面。一是对词进行价值判断,二是对词进行审美判断。罗大经词话偏重从价值判断出发对词家和词作进行探讨,所以弥散着浓厚的道德伦理的气息,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内涵。罗大经词话还考察了词的审美意象,从鉴赏论角度理解词所包含的美学魅力。罗大经词话还从语言音韵的环节探索词的艺术美表现,这样的研究具有实证性和可操作性的意义。
刘克庄鉴赏词作,敢于进行否定性的评论,无论作者是否为名家、地位显赫者,他表现出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个性。他的否定性批评,一是涉及对于前人词作的某些话语的模仿或“掉书袋”现象,二是关系到“崇性理而抑艺文”的狭隘的道德批评的思潮。正是由于不满于流行的道德批评,刘克庄以自我的努力在词话中进行审美的艺术批评。
陈郁词话,从“痛苦”这个情感因素揭示出诗词写作的一个主体动因。痛苦的经历与体验有助于形成道德高尚、灵魂崇高的人格,而这又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它们形成一个紧密的精神链条和情感逻辑,使文学产生永久不衰的热情冲动和心理张力。陈郁的词话思想包含辩证发展的因素,尽管对前人的佳作予以肯定,但是没有墨守对经典的迷信和崇拜,而是以动态的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艺术的进步,因此获得的结论比较客观和具有创见。他认为周美成“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在文本的影响和传播的意义上超越了古人的经典,不能不说是审美和艺术的进步。陈郁意识到,对于前人的借鉴与超越,才可能使文学薪火相传,繁荣发展。而结合历史现实考察,两宋的国家制度或皇权政治给予文士词人的优厚待遇也为他们超越前人、繁荣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物质保障。
周密词话在理论意义上主要牵涉词与民俗的关系、词的文学继承性这两个方面。周密对词表现民俗内容予以肯定,意识到词这种文学形式对于民俗美表现的艺术特征。对词的文学继承性,周密从修辞美学的角度,肯定词在语言修辞方面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主要包括这几方面内容:
审美创造论。沈义父对词的思考主要围绕创作这个轴心展开,《乐府指迷》开篇即论“作词之法”。然而,这又并非拘泥在具体的写作技巧方面,而是从审美创造的艺术视界,首先为词的创作设定可供参照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概念,并且从理论上相应规定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由此开始对词学的思考,并且将思考上升为理论的概括,形成了自我的艺术概念。沈义父为词界定了四个审美创造的原则,即“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首先,从形式上规定必须符合音律。只有“协”律,才能使词的审美特性显现出来,不然则成为长短之诗。其次,从审美理想上确立“雅”的目标。此处的“下字欲其雅”,不仅仅局限在语言传达的意义上,而是包括语言表达在内的整个词作的思想意蕴,这个“雅”,既指语言,又指由语言所表现出的文本意义、风格等方面。再次,从传统的艺术观念出发,对词的审美风格作出描述。“用字不可太露”,这一方面涉及艺术传达的技巧,是从语言表现角度强调词应追求字面的曲折委婉;另一方面涉及美学观念的取向,以空灵含蓄作为艺术的价值旨归。后者呈现更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传统诗论讲究“含蓄美”,它既是审美风格的指向,又作为艺术创造的技巧。刘勰推崇“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并将之界定为“隐秀”[2]。司空图心仪诗歌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将“含蓄”作为艺术美的构成之一。严羽欣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趣味。确切地说,《乐府指迷》的这一看法是对上述美学观念的继承。最后,从思想内容的表现方面,主张“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这则看法,从美学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创见。沈义父不赞成“发意太高”,一方面是和他主张词的创作应该“含蓄”的观念相对应;另一方面则表明,他也不赞成词的思想意蕴过于“狂怪”,有违传统的伦理道德,或者一味地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带上明显的说教色彩。而是倾向词的意蕴要“柔婉”,要注重审美特性。
艺术技巧论。《乐府指迷》对艺术的技巧问题十分重视,将之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沈义父的艺术技巧论,既有从普遍的美学意义上论述词的创作的内容,也有从具体的写作方法的角度,思考一些技术性的表述的环节。《乐府指迷》的“技巧论”,占整个篇幅的大部分,词话总共二十九则,它占去二十则之多,可见作者对其重视的程度。沈义父的技巧论可大略划分为结构方面、语言修辞方面、咏物与用事方面、音韵格律方面等。
辩证的词学眼光。沈义父的词家论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仅有几则,但精练概括,切中要害。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他对每一词家纵论得失,以辩证的方法贯穿其中,可谓词话上的先例。
沈义父的《乐府指迷》,标志着南宋后期词话的新的水准,显示了词话这一批评样式的渐趋成熟。但它的缺陷是,在注重审美批评和艺术价值的判断的同时,忽略对词作和词家进行社会历史的批评,因此对现实的思想内容缺乏关注,由于重形式轻内容而导致在思想性上缺乏深度。
对于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的分析是刘壎词话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词的写作同样是主体心理结构以话语隐喻的方式所表达的情感与意义。因此,对于创作主体的心理气质的认识尤为必要。所以,刘壎认为创作主体的“气象”对于词的意境格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刘壎词话体现出辩证思维的意识,注重从审美角度分析文本的艺术特性、意境情趣、修辞技巧等方面的构成,不囿于对名家的崇拜,辩证地分析他们词作的不足之处,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批评范例。
张炎积累了丰富的词的创作经验,又有艺术家的悟性与灵感,“诗有姜尧章深宛之风,词有周清真雅丽之思”。张炎的人生,蕴含了历史的悲剧意识,也包容了诗性的情怀。他晚年撰写的词学理论著作《词源》,呈现诗与思交融的心灵历程,将丰富的艺术感悟和严谨的逻辑思辨完好地结合起来,可谓体大思精。既建立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一系列逻辑范畴、美学概念,又深入具体地研究了词之创作与欣赏的诸多问题,使词之探讨进入崭新的境界。《词源》的理论构成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音律论。张炎一方面将传统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移植到词的音律理论的阐发,以探求构成世界本源的五种元素“土、金、木、火、水”如何影响音律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寻找出社会历史制度等现实性存在的“君、臣、民、事、物”与之相对应,以形成一个符合主观逻辑的理论模式。然后,进一步引入儒家的“信、义、仁、礼、智”的道德伦理原则,使其获得和传统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理性结构。在此基础上,为五音的生成找到一个完整而精致的逻辑起点。最后,依据五音的规定性,具体确立了各自存在的特殊性。张炎以五行说为思维圆心,辅佐以儒家哲学的人伦原则,以五音为经纬,勾画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符合主客观逻辑的音律生成过程及有其内在特性的理论圆圈,建立了自我音律论的思维基石。
其次,张炎凭借华夏文化世代相传的家庭人伦原则和宗法礼教习俗等逻辑规定性,以富有创见力的想象和精致的理念模式,推演出家族血缘和十二阴阳律吕之间的潜在联系。他寻找自然现象和人伦原则的契合点,以获取一种和谐的物质世界和礼法制度的辩证统一的说明,他以这一美学观来阐明:律吕的内在规定性和家族人伦的规定性是如何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权力意志”和“生命冲动”,构成精神文化产生的客观基质和深层本体。无疑,张炎在这里贯穿的是理性逻辑,采用的是主观命意的理论推演,有天人感应的哲学色彩,但他所勾画的思维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音乐律吕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特性,给后世以极大的思维启示。
词的起源和审美特性。和王灼相同,张炎从历史主义的视界考察词的起源,但他似乎更侧重从音乐的角度确立词的起源问题,他甚至将诸多的文学样式界定为来源于“雅正”,可见他把音乐和文学的密切程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他确立了词之诞生的具体时间表,并以周美成为轴枢勾画出词之演变和发展的轨迹,由此为契机,他进一步论述词的审美本质的问题。他甚至对周美成这样的音律大家都存有微词,批评其“而于音律,且间有未谐”。可见张炎对词的音律问题最为眷注,他将词的形式美首先定位在音律的层面上。“故平生好为词章,用功逾四十年,未见其进。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僭述管见,类列于后,与同志者商略之。”在这表露心迹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张炎对于词的音律及其审美本质的殷殷之情。应该说,张炎对词的审美本质的注意甚至超过对词的起源问题的关注,他所思考的问题更为深入和具体,已提升到美学理论的高度。
词的审美理想。对这一问题,张炎探讨较多。张炎提出两个对立的范畴:清空与质实。前者作为其艺术的审美理想的核心概念,它既是张炎的美学价值取向,也是其判断词作的批评标准,是引导词之创作和欣赏的先行规定;后者则作为前者的对应性的负面存在,是与前者相背离的创作倾向,它为前者确立了一个可供否定的对象。两者的规定性自然地构成一个逻辑相承的辩证关系,从而上升为理论思维的抽象,这标志着其词话理论思考的自觉和成熟。正是上述美学范畴和艺术核心概念的提出,显示了《词源》区别于以往词话普遍上只沉湎于描述现象或罗列事实而忽略进行理论分析与逻辑抽象的思维特征。正是上述思维方式的确立和艺术标准的阐释,呈现了《词源》作为美学理论的存在价值。
艺术创造论。在审美理想这一价值杠杆的引导下,张炎进一步探讨词的艺术创造的问题。应该说,张炎不同于以往词论家的长处是,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又富有艺术家的灵感和悟性。所以,他论词能使理论和实践相融合,时有独到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张炎的艺术创造论涉及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
内容方面。《词源》提出“意趣”的概念,将之界定为词创作的首要准绳。艺术创造的首要原则是,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具有新的意蕴和趣味,不能重复别人的思想和语言。这表明张炎主张词之创作必须具备独创、高远的意趣,强调词人审事立意的重要性,词尚雅正的美学观念首先被规定为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创新和语言表现形态方面的求变。“不蹈袭前人语意”,就意味着在创作上提出思想和语言的双重独创性的要求。应该说,张炎在这里明确地提出艺术的“不可重复”的美学原则。其次,张炎提出“精思”的原则。他认为在词的创作过程中,“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兼得,则可造极玄之域”。张炎的“精思”原则,从文艺学的观念来看,就是强调艺术构思的精致和深入,以思想内容为先导,以巧妙独创的意境为轴心,达到审美创造的目的。张炎同时认为,“精思”为本,而“语句”“音谱”的要求为末,可见,他并不主张“以文害辞”,为了审美形式而牺牲思想内容,为了合律而忽略意趣神韵。但张炎的看法是辩证的,对后者也不忽略,他认为在“精思”的前提下,“二者兼得,则可造极玄之域”,从而达到艺术美的理想境界。再次,张炎对词的情感表现问题提出独特的看法,呈现出一定的美学价值。
形式方面。犹如对于内容问题的重视程度一样,张炎对于词的创作的“形式”这一极也十分关注,包含诸多甚启人思的观点。主要包含制曲、句法、字面、虚字等方面。
艺术技巧论。张炎的艺术技巧论牵涉用事、咏物、令曲、韵律等方面,均有诸多的精湛之见。
鉴赏论。张炎的鉴赏或评价的主观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清空、意趣、精思。这个标准,既是创作的美学要求,也是鉴赏的艺术尺度。而统摄这个标准的核心即是所谓的“雅正”。张炎对词家词作的鉴赏,多持客观公允的态度,不尚情绪化的偏激,注重以作品说话,将鉴赏与批评更多赋予审美的理念之中,也鲜明地体现了“雅正”的艺术趣味。
如果说张炎的词话还存在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因其作者过于沉湎于纯美学纯艺术的理论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对词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有所忽略。
总而言之,南宋后期词话表现出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呈现理论探讨的系统和深入,有些词话具备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核心概念,具有自我的方法论和理论风格,为后世词话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