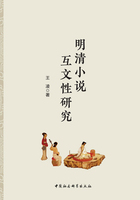
第4章 《绪论》:现代互文性理论概述
一 互文性概念解析及互文性理论流变简述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基础上首创的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克里斯蒂娃本人对这一概念曾经有过多次重要界定,如:“任何文本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的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概念,诗性语言至少能够被双重解读。”[17]“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对于认识主体而言,互文性概念将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潜入历史的方式。”“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18]克里斯蒂娃强调任何文本都不会孤立存在,因为文本意义的产生取决于“作家主体、接受者主体和已经成型的大量文本共同作用于某具体文本空间”[19]。如果将作品产生与传播的整个文化背景理解为广义文本,那么任何文学作品都将以“互文本”的形式存在。以上这几段文字被中外学者反复引用,成为互文性理论最经典和权威的解释。互文性概念提出后得到克里斯蒂娃身边师友的肯定、阐释和发展,渐成理论流派,其中尤以她的老师罗兰·巴特和她的丈夫索莱尔斯影响最大。索莱尔斯不仅在其文学创作中广泛实践“引文的拼贴”,而且也对互文性概念有过直接阐释和推广,他说:“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20]罗兰·巴特在理解互文性问题时则更倾向于解构,他认为,“一篇文本可以渐渐与其他任何系统关联起来,这种文际关系无任何法则可循,惟有无限重复而已”,而对于作者则不应“使其个人成为主体、根基、起源、权威和上帝”[21]。这种理解与其“作者已死”观念基本一致。罗兰·巴特后来还在《通用大百科全书》词条中以较长篇幅对互文性进行了界定。此一阶段为互文性理论的初创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互文性理论经过发展逐渐出现分化,一派走向解构与文化研究方向,亦称广义互文性理论,除了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之外,耶鲁学派成为重要阵地;另一派为诗学和修辞学方向,亦称狭义互文性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托多罗夫等。广义互文性理论将互文性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旨在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狭义互文性则关注文本之间的各种具体关联,尤其是可作实证分析的引用、改写、影射、戏拟等互文技巧,如热奈特按从具体到抽象、个别到一般、局部到整体、显性到隐性的顺序将“跨文本性”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互文性(共在关系)、副文本性(邻近关系)、元文本性(批评关系)、超文性(派生关系,有时也称“承文本性”)和统文性(类属关系)。[22]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狭义互文性往往具有更高的可操作空间。
克里斯蒂娃对普遍互文性现象的发现是在多方影响下完成的,她个人最为推崇也多次提到的首先是巴赫金思想。巴赫金“关于语言相对活跃的发现启发了克里斯蒂娃等人对文字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家隐退现象的重视”[23]。巴赫金认为每个独立个体都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就是对话发生的前提。因为自我本身无法反观本体,必须借助他者来进行评判,[24]这就是自我与外界对话的开始。而生活的对话性又来自语言的对话性,因为除了第一个来到世界的孤独之人外,每个人在开口之前都已经接受了大量他人的话语,因此每个人的话语中总是无可避免地充斥着他者的声音。他甚至认为:“生活从本质来说是对话的。生活就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人的一生都是在参与这种对话,他自己的一切都处在话语之中,而这个话语又处在人类生活的对话网络里,处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讨论之中……世界的物质模式转化为对话模式。”[25]语言的对话性反映的是思想的对话性,作为思想媒介的文本自然也时刻处于这种对话模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间主观性”被发掘出来。西川直子指出:“所谓间主观性,是指在不同的复数主观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的场被打开的事实,使间主观性的观念向文本的平面移动的,就是间文本性。”[26]这样一来,互文性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
同时,互文性理论的形成也得益于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在探究语言结构时所秉承的“关系性思维”当是索绪尔对于互文性理论的最大贡献,除此之外还有他对语言符号“差异性”的认识。索绪尔认识到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任意、随机的,靠约定俗成的习惯才得以固定。这“通常表现为某种发音或某种拼写的能指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的凸现需要其他能指的参与”[27],这也就是语言的“非指涉性”。“作为言语主体的个体自身既不能够创造也不能够修正语言,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集体的强制力量,为了交流,我们必须全盘接受既存的语言系统。”[28]“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29]同时,索绪尔又认为:“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30]从逻辑上说,差异是通过比较得出,而比较则首先必须将对象进行普遍联系,所以差异性与关系性思维直接相关。语言符号的关系性决定了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文学文本具有同样的关系性特质。这种关系性和差异性思维对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导致了20世纪学界的语言学转向。
克里斯蒂娃从索绪尔的语言研究中除了借鉴“关系性”和“差异性”思维之外,还得到了“字谜”研究的相关启发。“字谜”研究是索绪尔晚年重点关注的内容,其研究对象是“传达某种意义的一串文字由于顺序改变而产生别的意思”[31],“通过调整一串具有固定意义的文字中字母的顺序而组合出新词”的现象,又被称为“易位构词”[32],或“易音铸词”[33]。这种现象的实质在于“附着在单义性意义作用线上的符号部分的要素(声音、文字)同时创造出其他的意义”[34],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索绪尔通过这种字谜游戏发现了“诗是双层的,行上覆行,字上覆字,词上覆词,能指上覆能指”[35],这种现象用索绪尔原来的结构主义无法解释。克里斯蒂娃将这种“作为符号和结构的扭曲”而产生意义的微观语言现象进行放大(由线性的句子扩展到面状甚至立体的空间)和移植,这才触及了文学文本以及社会历史文本中的互文性。
除此之外,克里斯蒂娃还多次提到她的互文性思想形成也受到来自东方文化的影响,她说,“就在我把巴赫金思想引入法国之时,我发现了一位名叫张东荪的中国学者的研究”[36],“东西方有两位学者都指出了运用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来分析语言时产生的缺陷,这绝非偶然。一位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张东荪(Chang Tung-Sun),提出了一种语言学范畴(即表意字)。在那里,阴—阳‘对话’取代了上帝;另一位是巴赫金,他试图在革命的社会中通过一种动态的理论建构来超越形式主义”[37]。张东荪曾在其《思想言语与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名学)可称为“相关律名学”或曰“两元相关律名学”,其特点是“有无相生、高下相形、前后相随”,他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简单来说,中国古人秉承的是一种万物皆有联系、对立的事物之间也可以彼此变通转化的思维方式。此外,张东荪还指出了国人不关心“主体”,而注重“现象”(或曰“泛象论”)的秘密,他认为:“《周易》在哲学思想上只是用‘象征主义’(sumbolism)来讲宇宙万物的变化即所谓‘消息’是也。”“八卦以及六十四卦都是用象征来表示变化的式样。不但对于变化背后有否本体不去探究,并且以为如能推知其互相关系则整个儿的宇宙秘密已经在掌握中了。又何必追问有无本体为其‘托底’(substratum)呢?”[38]这种思维方式与索绪尔的关系性、差异性思维其实具有很大相通性。而这一信息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中国古代所具有的诞生互文性观念的思想条件。事实上,古人创作中的很多现象都直接体现传统哲学中的关系性和差异性思维:古人作诗讲究炼字,王安石通过比较“绿”“入”“过”等词的差异,最终确定“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组合;贾岛在“推”“敲”之间反复权衡,才选择了“僧敲月下门”的表述,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炼字”游戏,不正是在语言的组合轴与聚合轴上寻找最佳选择的实践吗?《文心雕龙·练字》表示文学创作有时要避免“同字相犯”,有时却又“宁在相犯”[39],具体的选择则要依据特定的语境,这与明清小说评点中屡屡提及的“特犯不犯”“同而不同”意思接近,这种犯、避之法不也是古人创作中重视语言、意象甚至情节之间的关联与差别的直接表现?另外,我国古典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所追求的多义性是否与巴赫金的“双值性”具有一定关联?古人在创作中强调“征圣”“宗经”,鉴赏活动中又强调“秘响旁通”“交相引发”,这也是重视文本之间广泛联系的表现。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否告诉我们在互文性问题上中西方具有天然的对话空间?
二 互文性理论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互文性理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已形成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文学理论。也差不多就在此时该理论伴随结构主义进入中国,随即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于20世纪末形成理论研究的高潮。张隆溪、张寅德、李幼蒸等最早从80年代开始对互文性理论成果进行翻译介绍。90年代有学者开始对互文性理论展开系统研究,殷企平《谈“互文性”》(1994)、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1996)、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1999)等文章皆为其代表。这一阶段学者们已经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对互文性产生了新的认识,如陈锡麟对互文性概念作出如下界定:“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引、暗引、拼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40]可谓既保留了广义互文性对文本现象的宽泛认识,也兼顾了狭义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的实际操作性。进入21世纪,学界不仅持续对国外互文性研究著作进行了大量翻译,而且也将对理论本身的认识推向纵深,其成果以《热奈特文集》(史忠义译)、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等作品的翻译和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2002)、王瑾《互文性》(2005)、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2014)、全虹《互文性的内涵与外延(朝鲜语版)》(2019)等专著的出现为代表。除对理论本身内涵及发展流变等表现出的极大兴趣之外,学界目前还将互文性作为重要工具与方法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自1983年张隆溪发表《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国内最早介绍互文性理论的学术成果)一文至今,以“互文性”为关键词检索,被中国知网的相关期刊收录论文达4600余篇;被收录读秀资源库的专著达53部,可见其研究之盛。
2012年克里斯蒂娃应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项目邀请来华讲学,其演讲内容被收入祝克懿所编《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一书。克里斯蒂娃在复旦讲学期间曾有国内学者向其介绍中国古人对于“文”的理解,即“文,错画也”(《说文解字》),古人认为线条、色彩、声音等的交错皆可产生“文”,“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克里斯蒂娃惊奇之余表示中国古人“对于文本的理解极具开放性”,并已形成相应的理论总结,大大超越同时期西方对“文”的理解。这一中西学者当面就文本问题进行交流的情况被记录在刘斐《中西传统互文研究——兼论中西互文的对话》(2012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克里斯蒂娃本人的承认,可知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相关理论命题与现代互文性理论存在某种事实的相通绝非虚言,在互文性问题上进行中西对话研究是可行也是必要的。事实上,这种研究从互文性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之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Intertextuality概念刚被翻译成中文时曾有多种译法,如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文际关系、间文本性等,但在众多翻译中最受研究者青睐的则是与现有中文修辞术语重合的“互文”一词。这本来仅仅是一个巧合,却因为“互文”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殊内涵而引发了中国研究者的无尽联想与遐思,阐释者借助这一巧合在中国的“互文”与西方的“互文”之间展开了某种跨语言、超时空的“能指”对话。如有学者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提出思考:中国传统文献中“互文”所指称的语言现象是否等同于互文修辞?若如此,则“互文”一词是否能够承载intertextuality的全部内涵?抑或修辞仅仅是传统互文的类型之一?沿此思路,中国传统文论中是否还有其他话语也表达了互文性思想?张隆溪《道与逻各斯》(1998)、周裕铠《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2003)、史忠义《中西比较诗学新探》(2008)、赵渭绒《西方互文性对中国的影响》(2012)等专著都曾有一定篇幅回应这些问题。截至当下,刘斐的专著《中国传统互文研究》对中西互文问题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探究;胡作友和杨杰《互文·复调·创生——〈文心雕龙〉的异域重生》、陈颍《古代文论中的“互文性”言说》、张颖《汉字与“互文性”——克里斯蒂娃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国维度》、杨洋《中国古代诗学经验中的互文性探究》(以上论文皆发表于2019年)等则为中西互文对话的最新成果。
三 中国传统“互文”概念
中国的“互文”概念由来已久。据考证,作为“前后语言单位之间交错省略、互相补充,需要合在一起才能表达完整语义”的特殊语言现象在东汉末年已被郑玄发现。[41]服虔在《左传》注中针对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的表述,指此为“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见”。“互相见”当为互文的最早表述。不过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第四》等提供的信息,服虔所注《左传》极有可能受郑玄影响,又加之郑玄在其《三礼注》《尚书大传注》等书中也将“互文”“互言”“互辞”“互见”“互相明”“互相备”等作为固定术语反复使用,所以学界一般都以郑玄为互文修辞的最早发现者。[42]在郑玄的注释中,这种“文(辞)之间具有互动关系”的语言现象,具体又表现为义类互举、互文辞格、缩略互文与推理互文四种不同情况:其中义类互举指在句子中列举同类现象;互文辞格则表现出上下交错而省文的特点(既可存在于同一文本之内,也可存在不同文本之间);缩略互文指在当下文本中对源文本进行缩略表达;推理互文则是根据源文本所提供的制度原则进行类推,并在当下文本中形成结论。[43]与其说互文是解经者为方便阐释经典而发明出来的特定术语,毋宁说互文是汉语表达中本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这四种互文类型,在古代文学创作中都能找到不同的运用和发挥的例证。其中以修辞意义上的互文运用最为人们熟知。可见我们以往仅仅将其理解为文本之内(一句之内或是句子之间)的微观修辞,其实并不符合互文概念的原始含义。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互文概念的内涵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作为微观修辞的语言现象,其使用范围也并非仅限于单个文本之内,其互文项的层级涉及词组、小句、句群直至文本,既有文本之内的联系,也包括了大量的跨文本语言现象。
至唐,贾公彦开始对传统互文进行自觉的理论总结,他严格区分了郑玄注中的“互文”“互相备”“互相足”等说法,将互文概念提炼为“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的语言现象,进而提出理解互文现象的“互见为义”原则,强调各互文项只有结合在一起方能完整表意。[44]这对互文现象的形成及理解机制都是一个突破性总结,然而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即将互文形成过程仅限定在互文项之间交错省略而成文的一种类型,就使得互文概念的内涵大大缩小。清代俞樾对传统互文重新思考,其关注对象超越互文辞格再次涵盖到同指互文、类义互文、缩略互文和推理互文等不同类型,而且在此基础上将互文现象的理解机制进一步总结为“参互见义”,[45]为我国古代互文观作出了最全面而深刻的总结。现代语言学家郑远汉在综合贾公彦、俞樾互文成果的基础上,又对互文提出了“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的定义,[46]从此成为现代学界对互文修辞的权威解释。但这也使我们对互文的看法重新回到贾公彦所限定的修辞之路上。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传统训诂学意义上的“互文”概念与西方理论视野中的intertextuality有同有异。中国原始互文概念虽然在互文项的位置和规模上内涵比较宽泛,但从后世的使用情况来看多重视其作为修辞的意义,也就是关注语篇之内甚至句子之内的微观互文现象;而西方互文性理论虽然也将文本之内的“交叉参考方式”视为互文现象(“内互文”)之一,[47]但更为关注的仍是语篇、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有学者看到了二者区别,极力强调“互文是一种语法修辞方式,它是一个语篇(文本)内的东西”“互文性是语篇间性(文本间性),与互文根本无关”,并主张以“语篇间性”取代互文性。[48]这种说法似乎也过于偏激,因为无论如何,中西互文观念在意义的生成机制及理解机制上存在的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都比较关注语言形式上的相互对应和语义上的参照、补充,西方互文认知机制中的“联想嵌入即互文”原则实与传统互文观中的“相似即互文”“互补即互文”内涵有着天然的联系,[49]因为相似或互补的内容、形式往往是引发联想的重要契机。概念的解析与梳理为中西互文观念的沟通、比较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不过,我们如果跳出具体修辞的局限,以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内涵为参照对中国文学中的相关命题进行搜寻与甄别,是否会有新的发现?虽然这种做法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但也确是两种思想进行沟通对话的必要步骤。随着学界对这一研究的推进,发现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个庞大而又清晰的互文话语系统。在我国传统的创作论与阐释学中,互文性从来都是作为非常有效的原则被加以运用。这一内容将在本书第一章详细分析,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