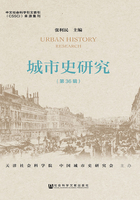
·市政建设与社会控制·
清末上海印度巡捕的复杂面相
——以印度巡捕的罢工为视角
内容提要:在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租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管理租界,西方现代城市管理经验被引入上海,巡捕房的建立更是引入了现代警察制度,1880年代,巡捕房开始引进印度巡捕。印度巡捕几乎建构了当时人们对于“十里洋场”治安管理的典型外在印象。上海租界、西方殖民者以及既被殖民又是城市秩序维护者的印度人,三者之间关系复杂。本文将再现印度巡捕形象,从英印关系的角度梳理清末上海印度巡捕的数次罢工,以及罢工背后的经济原因,分析国人对于印度巡捕罢工的民族主义想象。
关键词:公共租界 巡捕房 印度巡捕 罢工 民族主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上海的地位极其重要。自1840年代以来,随着贸易的繁荣和租界的建立,上海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从煤气、电灯、自来水到三权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再到道路行车规则、垃圾倾倒规定,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经由上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在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租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管理租界,西方现代城市管理经验被引入上海,巡捕房的建立就是公共租界引入现代警察制度的一种尝试,对租界治安有着积极影响——警察制度可以有效地制衡地方上的精英,以建立有效对租界的统治。
在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租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管理租界,西方现代城市管理经验被引入上海,巡捕房的建立就是公共租界引入现代警察制度的一种尝试,对租界治安有着积极影响——警察制度可以有效地制衡地方上的精英,以建立有效对租界的统治。 印度巡捕(简称印捕)正是这种尝试的结果之一,他们不仅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同时还作为现代制度的代表出现,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身处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进程之中。印捕并非上海那段历史的煊赫主角,却几乎建构了当时人们对于“十里洋场”治安管理的典型外在印象。
印度巡捕(简称印捕)正是这种尝试的结果之一,他们不仅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同时还作为现代制度的代表出现,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身处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进程之中。印捕并非上海那段历史的煊赫主角,却几乎建构了当时人们对于“十里洋场”治安管理的典型外在印象。
印捕并非城市的直接管理者,而是隶属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一个由英国人主导的机构,而英国当时是印度的宗主国。对印捕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完整再现上海城市风貌,还可以折射英帝国与其殖民地印度之间的关系。急剧步入现代化的上海、作为帝国主义和现代文明代表的西方人以及被殖民又是城市秩序维护者的印度人,这一以印捕为主线的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乃是本文主要的关怀。
一 身影模糊:学术史中的印度巡捕形象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战争硝烟虽然弥漫于中越边境及闽台等海疆之地,但紧张气氛却蔓延到了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外国居民不再信任已经为他们服务了十余年的华捕,而希望雇佣非中国籍的巡捕。出于费用的考虑,工部局又不愿意引入欧洲裔的西捕。 妥协的结果是聘请印度人来充任巡捕。是年10月下旬,第一批印捕从香港出发,来到上海。
妥协的结果是聘请印度人来充任巡捕。是年10月下旬,第一批印捕从香港出发,来到上海。
有位研究在上海的印度人的学者指出:“但凡读过比利时著名的漫画家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的人,都会对于上海公共租界的锡克人巡捕耳熟能详。” 《丁丁历险记》关于上海的这一章节大约创作于1934年。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的一个欧洲漫画家看来,印捕几乎可以作为上海公共管理力量的一个主要象征而存在,但是自1884年印捕出场至抗战时逐渐退场期间及其后,学界对印捕的研究比较稀少。
《丁丁历险记》关于上海的这一章节大约创作于1934年。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的一个欧洲漫画家看来,印捕几乎可以作为上海公共管理力量的一个主要象征而存在,但是自1884年印捕出场至抗战时逐渐退场期间及其后,学界对印捕的研究比较稀少。
19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主要是上海研究的热潮兴起。据统计,1980~2003年这20多年间,仅仅海外关于上海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就已经不下300篇,著作不下50部。 而近十年来关于上海史的研究更显突出。同时,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关于租界警务管理的章节得到了细化,并且有涉及印捕的介绍性内容。
而近十年来关于上海史的研究更显突出。同时,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关于租界警务管理的章节得到了细化,并且有涉及印捕的介绍性内容。 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历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原先社会的中下层,
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历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原先社会的中下层, 以及边缘群体,进而发掘了一批未被利用的关于上海巡捕的档案,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上海的地方志也值得参考,当代《上海公安志》
以及边缘群体,进而发掘了一批未被利用的关于上海巡捕的档案,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上海的地方志也值得参考,当代《上海公安志》 中对于印捕数量及其薪金待遇等都有详细描述,且史料多来源于租界华文档案,比较翔实可信。
中对于印捕数量及其薪金待遇等都有详细描述,且史料多来源于租界华文档案,比较翔实可信。
同时也出现了针对租界巡捕的专题研究。英国的毕可思(Robert Bickers)在《谁是上海的巡捕,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 中,直接以上海租界巡捕作为研究对象。另一位关于外国巡捕的研究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晓明,她的博士论文题为《上海法租界的警察》。
中,直接以上海租界巡捕作为研究对象。另一位关于外国巡捕的研究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晓明,她的博士论文题为《上海法租界的警察》。 她注意到了和印捕地位颇为类似的越南巡捕的问题,并且讨论了法国殖民者与越捕的关系以及越捕的工作情况,这对于我们探讨印捕提供了重要借鉴。
她注意到了和印捕地位颇为类似的越南巡捕的问题,并且讨论了法国殖民者与越捕的关系以及越捕的工作情况,这对于我们探讨印捕提供了重要借鉴。
和本文讨论内容直接相关的是杨倩倩的硕士论文《上海公共租界印度巡捕研究初探,1880~1930》。这是中文世界第一个针对印捕的专题研究——距离第一位印捕站在上海大街上的1884年,已经过去了130年之久。该文作者大量使用了新近整理出版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和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等史料,并对相关材料做了比较好的梳理,对于印度巡捕在公共租界的设立、招募、待遇、升迁等事宜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她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工部局对印捕的管理和控制”。 也就是说,该文站在工部局管理者的视角,而非印捕的视角,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希望予以突破的。
也就是说,该文站在工部局管理者的视角,而非印捕的视角,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希望予以突破的。
综合考察既往有关上海印捕的研究,人们关注的仍然是一种广义上的殖民地管理行为,但是对于这一群体自身的情况,以及作为被管理者的普通居民对印捕之印象的研究都极为匮乏。研究印捕这一群体的困难在于,他们多半没有文化,也鲜有关于他们的书信材料问世——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往往来自殖民者对他们想法和声音的记录,而这样的记录注定是带有殖民者的偏见的。不过,尽管作为被殖民者的印捕不能直接书写历史,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历史的书写者对于印捕的存在进行加工、规训和建构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极其重要的研究内容。研究这个渗透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究权力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体现为英国人和印度人的互动以及印度人和中国人的互动。
二 英—印关系:以印捕罢工为中心的探讨
在研究上海租界的印度巡捕与作为管理者的英国人之间的互动时,需要先厘清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上海的统治究竟是以何种形态进行的。如果按照眼下中国主流话语来说,租界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也就是说,租界是殖民地的一种形态,其论证是基于中国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但如果要确认租界确实是殖民地,就还需要了解当时统治者自身的想法。表面上看,和传统的殖民地管理模式
也就是说,租界是殖民地的一种形态,其论证是基于中国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但如果要确认租界确实是殖民地,就还需要了解当时统治者自身的想法。表面上看,和传统的殖民地管理模式 不同的是,在上海并不存在一个总督来代表帝国。并且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名义上在上海是和西方人分享租界的治权而不是像香港一样直接割让土地成为租界。那么上海租界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看西方人自己的说法——《1854年土地章程》生效以后,《北华捷报》的编辑就使用了“国际殖民地”这样的说法来评价新的英法租界的性质。
不同的是,在上海并不存在一个总督来代表帝国。并且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名义上在上海是和西方人分享租界的治权而不是像香港一样直接割让土地成为租界。那么上海租界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看西方人自己的说法——《1854年土地章程》生效以后,《北华捷报》的编辑就使用了“国际殖民地”这样的说法来评价新的英法租界的性质。 最新的研究表明,《1854年土地章程》并未明确赋予租界里的外国人组建政府的权利,但是时任英国总领事阿礼国故意对该章程第20条进行了扩展性解释并组建了工部局,使得租界脱离了上海道台的管辖。
最新的研究表明,《1854年土地章程》并未明确赋予租界里的外国人组建政府的权利,但是时任英国总领事阿礼国故意对该章程第20条进行了扩展性解释并组建了工部局,使得租界脱离了上海道台的管辖。 由此观之,可以将工部局对上海的统治形态视为殖民统治——站在租界管理者的角度亦是如此。
由此观之,可以将工部局对上海的统治形态视为殖民统治——站在租界管理者的角度亦是如此。
前文中曾经提到,印捕进入上海的原因是保护静安寺地区的西人居民,而在华人和西人均不合适的情况下,印捕作为一种可能的选项出现,恰恰是得益于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经验。面对不断扩张的殖民帝国,仅仅依靠英国人自身已经很难应付,这时较早被征服的锡克人就成了相比英国士兵更为合适的选择,他们的佣金更低而且表现也相当不错。 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属于英军的锡克族士兵就已经充分体现出其英勇善战、忠实可靠的一面。
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属于英军的锡克族士兵就已经充分体现出其英勇善战、忠实可靠的一面。 1867年,港英政府因为人手不足开始招募锡克族的印度巡捕,他们的工作得到了香港警督克列夫登的称赞。
1867年,港英政府因为人手不足开始招募锡克族的印度巡捕,他们的工作得到了香港警督克列夫登的称赞。 因此印捕在1884年出现在上海,也可以视为业已成熟的英帝国管理殖民地手段的一种顺理成章的延续。
因此印捕在1884年出现在上海,也可以视为业已成熟的英帝国管理殖民地手段的一种顺理成章的延续。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英国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印捕之使用,有正面,亦有负面。至于负面,印捕不但有违纪行为,更是出现了几次严重的罢岗(罢工)事件。
第一次罢岗发生于1891年8月,巡官卡梅伦在巡查老闸捕房时,发现该处印捕的床铺卫生极其恶劣,遂决定对该捕房所有印捕处以每人罚款3元,引起印捕不满,他们当即拒绝上班,卡德路捕房的印捕亦参与罢岗。 公共租界警备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提出罚款3元太重,改为罚款一日工资;今后再有发现,加重罚款。事情很快解决,印捕恢复上班。
公共租界警备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提出罚款3元太重,改为罚款一日工资;今后再有发现,加重罚款。事情很快解决,印捕恢复上班。
第二次罢岗发生于1897年3月19日,次日警备委员会主席列德就此事向工部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日的一些细节。 19日早上,印捕在操练时,下起雨来,带队巡长决定结束训练,改为让印捕上岗执勤,但被印捕拒绝,他们先到中央捕房,再到警备委员会,提出四点意见:(1)下雨天被派去操练;(2)巡长巴恩斯在操练时骂人,还夹杂粗话;(3)印捕未获得相应的奖励金,且没有臂章和合适的警服;(4)上级警官中没有印度人,无处诉冤。警备委员会经过一番讨论,逐一批驳、解释。
19日早上,印捕在操练时,下起雨来,带队巡长决定结束训练,改为让印捕上岗执勤,但被印捕拒绝,他们先到中央捕房,再到警备委员会,提出四点意见:(1)下雨天被派去操练;(2)巡长巴恩斯在操练时骂人,还夹杂粗话;(3)印捕未获得相应的奖励金,且没有臂章和合适的警服;(4)上级警官中没有印度人,无处诉冤。警备委员会经过一番讨论,逐一批驳、解释。
仅从工部局记录来看,无疑是因印捕自身不服管理而酿成罢岗事件,工部局方面本身并没有过错。但是这些描述还是有令人生疑之处——印捕如果不想下雨时操练,那么为何巡长让解散的时候却不愿离开呢?果然,媒体报道与英国人的说法有些不同。据《字林沪报》称,印捕不愿在下雨时出操,即下雨后,印捕才被要求出操,而非如工部局所说的,出操时下雨。而且出操后竟然又下倾盆大雨,印捕感到不满,前往工部局申诉。 这种说法显然更合逻辑。下雨后要出操应是一系列不满爆发的导火索。
这种说法显然更合逻辑。下雨后要出操应是一系列不满爆发的导火索。
印捕不肯上街执勤导致街面上出现了一些混乱,警备委员会于是决定严厉告诫罢岗印捕,当天下午4点如果不恢复执勤,将会被开除,但印捕仍不复岗。 警备委员会遂开除15名有前科的印捕,以儆效尤。随后印捕复岗,罢工失败。
警备委员会遂开除15名有前科的印捕,以儆效尤。随后印捕复岗,罢工失败。
第三次罢岗发生在1906年。公共租界的印捕听闻在美国、俄国当差每月工资可以高达60~80元,而在上海一般巡捕的工资只有16元,最多不过22元,于是很多印捕提出辞职。 工部局内部磋商,决定根据聘约加以阻止。
工部局内部磋商,决定根据聘约加以阻止。 眼见辞职被拒,印捕转而请求每月增加薪金10元。董事会调查了印捕在工部局储蓄银行的存款情况,认为由其存款数额来看,他们并不差钱,遂再次拒绝。
眼见辞职被拒,印捕转而请求每月增加薪金10元。董事会调查了印捕在工部局储蓄银行的存款情况,认为由其存款数额来看,他们并不差钱,遂再次拒绝。 辞职不成,加薪亦不允,印捕遂于9月30日罢工,巡捕房172名印捕中有103人罢岗,波及面很广,而且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主要是罢工印捕胁迫那些不愿意参与的同伴。
辞职不成,加薪亦不允,印捕遂于9月30日罢工,巡捕房172名印捕中有103人罢岗,波及面很广,而且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主要是罢工印捕胁迫那些不愿意参与的同伴。 工部局非常紧张,出动“西商团练”(即万国商团),将所有罢工印捕押解到英按察使署(法院)审讯。
工部局非常紧张,出动“西商团练”(即万国商团),将所有罢工印捕押解到英按察使署(法院)审讯。 10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发布指令,10名印捕被解雇并遣返印度,其余印捕复岗。
10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发布指令,10名印捕被解雇并遣返印度,其余印捕复岗。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罢岗发生于1910年,与此前罢岗不同的是,这次罢岗的起因不只是单纯的待遇问题,还涉及锡克族内部马尔瓦人(Malwa)和曼杰哈人(Majha)的冲突,最终结果仍然是鼓动罢岗的为首者被开除,警备委员会调整了印捕内部两个族群的巡长—巡捕比例,印捕复岗。
三 家庭与消费:印捕罢工的经济原因分析
从这些罢岗事件可以发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于印捕的罢工采取了比较强力的压制措施,并且在最终的解雇、抓捕之前,工部局基本上都会有一次警告。但是这些警告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印捕内部似乎相当团结,鲜有退出罢岗的人。这种团结或许和印捕的宗教信仰有关。印度巡捕都是锡克人, 而锡克人的传统就是他们内部社群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而锡克人的传统就是他们内部社群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而且有材料表明这种传统不但能给参与者施加道德和精神上的控制,还会动用一定的暴力手段。例如在1906年罢岗中,有位编号为130的印捕并未参加罢岗,于是其他参与罢岗的印捕在他下班时就强行把他关在储藏室里面。
而且有材料表明这种传统不但能给参与者施加道德和精神上的控制,还会动用一定的暴力手段。例如在1906年罢岗中,有位编号为130的印捕并未参加罢岗,于是其他参与罢岗的印捕在他下班时就强行把他关在储藏室里面。 另有3名印捕也是因为没有参加罢岗,在外滩遭到15名印捕的暴力袭击。
另有3名印捕也是因为没有参加罢岗,在外滩遭到15名印捕的暴力袭击。 罢工过程中在工人内部出现纠察队性质的组织,是常见的情况。印捕罢工中出现的这种内部暴力,说明其背后存在一定的组织力量。虽然受材料的限制,我们无法了解这种组织运行的方式,但是从第四次罢工涉及的派别斗争来看,锡克教本身的宗教组织力量和地缘性质的组织力量对于这次罢工起到了决定性影响的作用。
罢工过程中在工人内部出现纠察队性质的组织,是常见的情况。印捕罢工中出现的这种内部暴力,说明其背后存在一定的组织力量。虽然受材料的限制,我们无法了解这种组织运行的方式,但是从第四次罢工涉及的派别斗争来看,锡克教本身的宗教组织力量和地缘性质的组织力量对于这次罢工起到了决定性影响的作用。
而通过分析这些罢岗事件的动因,我们发现基本上都和经济问题直接相关。而工部局对于这些罢岗巡捕采取的最有力压制手段是经济的而非政治或者暴力的。一旦有巡捕被开除,其他巡捕基本上都会立刻复岗——印捕对于经济上的敏感,比同时期的中国工人更甚。 杨倩倩的论文考证了上海印捕加薪的情况,因为物价上涨,工部局曾数次对印捕进行加薪。最早发生在1917年,此后1921年、1927年又两次加薪。
杨倩倩的论文考证了上海印捕加薪的情况,因为物价上涨,工部局曾数次对印捕进行加薪。最早发生在1917年,此后1921年、1927年又两次加薪。 此前,1906年印捕罢岗的背景也是当时物价上涨,但是没有得到加薪。这是当时一些人认为的印捕罢岗的原因所在。
此前,1906年印捕罢岗的背景也是当时物价上涨,但是没有得到加薪。这是当时一些人认为的印捕罢岗的原因所在。 在此我们看到,随着工资的提高,印捕再也没有罢工过,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上海印捕罢工背后的经济因素。
在此我们看到,随着工资的提高,印捕再也没有罢工过,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上海印捕罢工背后的经济因素。
此外,印捕的收入似乎也没有那么不堪,至少比上海普通工人要高许多。 前文曾经提到,在1906年罢岗时,工部局曾对印捕的存款进行调查,认为他们存款的数额较大,比较富有。而有意思的是,根据几个印捕死亡后的情况来看,他们去世时的财产并不多。
前文曾经提到,在1906年罢岗时,工部局曾对印捕的存款进行调查,认为他们存款的数额较大,比较富有。而有意思的是,根据几个印捕死亡后的情况来看,他们去世时的财产并不多。 如果要对这种矛盾的现象进行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有必要分析印捕有哪些主要的开支,以致印捕在经济上的抗压能力如此薄弱。
如果要对这种矛盾的现象进行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有必要分析印捕有哪些主要的开支,以致印捕在经济上的抗压能力如此薄弱。
笔者认为,造成印捕经济压力的主要因素很可能是汇往家乡的钱款和购买性服务(嫖娼)的花费,而这两项支出都与“家庭”有关。对印捕来说,他们因居住在巡捕房营房而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孤身一人来上海,即使是已婚者也不得不离开在印度的妻子,实质上也过着单身的生活。 有人对锡克人出国工作的动机分析道:
有人对锡克人出国工作的动机分析道:
多数家庭既不富也不穷,其实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在乡村的地位受到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和土地价格膨胀的威胁。因此移民成为一项家族计划,一种为避免待在家乡地位下降而做出的体面选择。与其令家族所有土地进一步分割,不如让年轻人参军或出国来增加家庭财富和村中的地位。只有通过购买更多的土地,建造砖屋,为家中的女人安排体面的婚事才能做到。那些被派出的几乎全是单身汉或已婚而不带妻子旅行的年轻人。
前往上海任职的锡克族巡捕确实是家族中主要的经济来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曾经提到,大多数印捕每年都会把他们在工部局储蓄银行的钱汇往家乡, 而在提到这笔汇款的大小的时候,1916年《工部局年报》使用的词语是“可观的”。
而在提到这笔汇款的大小的时候,1916年《工部局年报》使用的词语是“可观的”。 虽然具体比率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把收入的一大部分都寄回了家,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某些时间拥有可观的存款,而在去世的时候却比较贫穷。这种模式有点类似于当下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模式,而其得以推行其实是英帝国(在中国则是中国政府)带来的现代化。若不是英帝国在印度各地和上海都建立了现代化的银行和邮政系统,那么外出打工者是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收入寄回家乡的。虽然英帝国并非出于道德而为这些印度人谋取福利,而可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建立的现代化的社会设施实实在在地为印捕提供了比留在家乡更好的选择。
虽然具体比率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把收入的一大部分都寄回了家,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某些时间拥有可观的存款,而在去世的时候却比较贫穷。这种模式有点类似于当下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模式,而其得以推行其实是英帝国(在中国则是中国政府)带来的现代化。若不是英帝国在印度各地和上海都建立了现代化的银行和邮政系统,那么外出打工者是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收入寄回家乡的。虽然英帝国并非出于道德而为这些印度人谋取福利,而可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建立的现代化的社会设施实实在在地为印捕提供了比留在家乡更好的选择。
离家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巡捕的性需求无法满足,在没有妻子或者女伴的情况下,可能的解决方式包括嫖娼、和本地的或者来自印度的其他女人形成比较长久的伴侣关系,以及强奸等暴力手段。除了嫖娼之外,剩下的两种方法都不太可行。诚如前文所说,锡克族人因其共同的信仰,通常容易形成联系紧密的团体,而这将构成对于中国女性和锡克男性婚姻上结合的强烈反对力量。 也有不少印捕铤而走险,采取暴力手段以寻求性满足,但是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对印捕来说有极大风险。以《申报》报道为例,通过《申报》全文数据库检索,自1883年印捕来沪,直至1949年,报道印捕性侵案件共29起。
也有不少印捕铤而走险,采取暴力手段以寻求性满足,但是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对印捕来说有极大风险。以《申报》报道为例,通过《申报》全文数据库检索,自1883年印捕来沪,直至1949年,报道印捕性侵案件共29起。 这些案件后来经法庭审讯后裁判,情节严重者如发生于1909年的印捕强奸车夫黄世仁案,涉案印捕直接被判处徒刑,
这些案件后来经法庭审讯后裁判,情节严重者如发生于1909年的印捕强奸车夫黄世仁案,涉案印捕直接被判处徒刑, 其余犯案印捕,也均遭到解职的处罚。性暴力反映的恰恰是对性的渴求,但是事后难免处罚。因此多数情况下,印捕还是会采取嫖娼这种风险较小的方法来满足性需求。印捕嫖娼而见诸报端的事例繁多,
其余犯案印捕,也均遭到解职的处罚。性暴力反映的恰恰是对性的渴求,但是事后难免处罚。因此多数情况下,印捕还是会采取嫖娼这种风险较小的方法来满足性需求。印捕嫖娼而见诸报端的事例繁多, 并有求欢不得殴伤妓女的事件发生,
并有求欢不得殴伤妓女的事件发生, 乃至于有一种说法认为,印捕“红头阿三”的“阿三”起源就和印捕嫖娼之事有关。
乃至于有一种说法认为,印捕“红头阿三”的“阿三”起源就和印捕嫖娼之事有关。
总之,印捕嫖娼的现象在当时颇为普遍。虽然印捕的工资较之上海当时的平均工资高出不少,但是根据美国学者贺萧对嫖娼价格的统计,嫖娼的经济压力对于印捕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因此,在去掉他们汇往家乡的那笔钱和嫖娼的花费之后,印捕的工资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印捕每次罢岗的核心诉求都是经济诉求,一旦经济诉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会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
因此,在去掉他们汇往家乡的那笔钱和嫖娼的花费之后,印捕的工资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印捕每次罢岗的核心诉求都是经济诉求,一旦经济诉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会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
四 国人对于印捕罢工的民族主义想象
相比英国的巡官们,印捕属于被管理者;相比当时公共租界的一般百姓,印捕则以管理者的面貌出现。印捕形象在国人脑海中的塑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超过了本文所能涵盖的范畴。但是就罢工这一特定问题来说,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印捕罢工的?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印捕服务于上海的时间段,恰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可是印捕对于这一运动似乎显得不冷不热,不但未曾见到他们以民族独立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巡捕队伍。 对于印捕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存在一种反抗英国统治的意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宽泛地使用了“印度”的概念。萨义德曾说,当我们使用“印度”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变相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的知识分类方法。
对于印捕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存在一种反抗英国统治的意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宽泛地使用了“印度”的概念。萨义德曾说,当我们使用“印度”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变相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的知识分类方法。 就当时情况来说,“印度”是一个只对英国殖民者有意义的概念,用来指代他们所控制的南亚次大陆的大片土地。但是实际上,这个“印度”是由多个彼此冲突或者隔离的地方性政权组成。位于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族人和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之间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冲突和敌视。在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锡克族人就一直受到印度教徒的迫害和压迫。
就当时情况来说,“印度”是一个只对英国殖民者有意义的概念,用来指代他们所控制的南亚次大陆的大片土地。但是实际上,这个“印度”是由多个彼此冲突或者隔离的地方性政权组成。位于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族人和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之间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冲突和敌视。在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锡克族人就一直受到印度教徒的迫害和压迫。 在英国入侵的过程中,锡克族聚居的旁遮普地区是最后被英军征服的地区。因此在两次英锡战争中,大量的印度教士兵加入殖民者军队,成为英帝国殖民旁遮普地区的帮凶。但英国人占领之后对锡克族采取的政策却是较为宽容的。他们兴建了很多基础设施,同时尊重锡克族的宗教传统——之前的莫卧儿王朝并未表现出这种尊重。英国相对开明的统治加上锡克族人和印度教徒历史上的仇恨,导致了在著名的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锡克族人坚定地站在了英国殖民者一边。十万余锡克族士兵加入英国军队,旁遮普地区的柴明达尔(领主)们也积极提供物资,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
在英国入侵的过程中,锡克族聚居的旁遮普地区是最后被英军征服的地区。因此在两次英锡战争中,大量的印度教士兵加入殖民者军队,成为英帝国殖民旁遮普地区的帮凶。但英国人占领之后对锡克族采取的政策却是较为宽容的。他们兴建了很多基础设施,同时尊重锡克族的宗教传统——之前的莫卧儿王朝并未表现出这种尊重。英国相对开明的统治加上锡克族人和印度教徒历史上的仇恨,导致了在著名的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锡克族人坚定地站在了英国殖民者一边。十万余锡克族士兵加入英国军队,旁遮普地区的柴明达尔(领主)们也积极提供物资,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 而锡克人也正是通过其出色表现获得了英国人的信赖。
而锡克人也正是通过其出色表现获得了英国人的信赖。
对于锡克人来说,由于印度民族主义中鲜明的宗教民族主义特性, 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印度独立”其实是不太认同的。举例来说,在1914年加德尔党人起义爆发后,一些人逃到了上海。英国人十分担心印捕受到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的蛊惑。
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印度独立”其实是不太认同的。举例来说,在1914年加德尔党人起义爆发后,一些人逃到了上海。英国人十分担心印捕受到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的蛊惑。 然而锡克族巡捕并未受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然而锡克族巡捕并未受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前文的分析也表明,印捕罢工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民族主义口号并未出现在他们的罢工诉求中。事实上,当时印捕普遍配备了火枪,甚至还有专门的骑巡队,其战斗力十分强大,甚至可以和军队媲美。
前文的分析也表明,印捕罢工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民族主义口号并未出现在他们的罢工诉求中。事实上,当时印捕普遍配备了火枪,甚至还有专门的骑巡队,其战斗力十分强大,甚至可以和军队媲美。 如果印捕罢工是基于民族主义而反抗殖民统治的话,那就断然不是开除罢工印捕就能平息了的。这一问题可以参考1915年新加坡的印度士兵爆发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情况,这些士兵与英军血战半个月,席卷整个新加坡,最终在沙皇俄国的帮助下,这次起义才被镇压。
如果印捕罢工是基于民族主义而反抗殖民统治的话,那就断然不是开除罢工印捕就能平息了的。这一问题可以参考1915年新加坡的印度士兵爆发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情况,这些士兵与英军血战半个月,席卷整个新加坡,最终在沙皇俄国的帮助下,这次起义才被镇压。 相比之下,印捕对工部局的反抗,无论是方式上还是烈度上,都较之真正的民族主义起义要温和得多,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本文前述印捕乃是基于经济原因罢工的观点。
相比之下,印捕对工部局的反抗,无论是方式上还是烈度上,都较之真正的民族主义起义要温和得多,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本文前述印捕乃是基于经济原因罢工的观点。
然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印捕背后的历史并不了解,而是简单地把他们当作和中国一样的被殖民的民族来看待。比如前文所引《申报》对印捕的报道,该报编辑就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兼有反抗殖民主义的意义。 而作家蒋光慈则在创作中描述了一名印捕把布尔什维克学生抓起来又释放的故事。故事中,这名觉醒的印捕意识到中国和印度同样是受到压迫的民族,都需要被解放,就此提出救中国即是救印度。
而作家蒋光慈则在创作中描述了一名印捕把布尔什维克学生抓起来又释放的故事。故事中,这名觉醒的印捕意识到中国和印度同样是受到压迫的民族,都需要被解放,就此提出救中国即是救印度。 另一位左翼作家杨邨人在1929年的《大众文艺》发表题为《红头阿三》的文章,文中作者也一改之前对于印捕的负面态度,塑造了一个和蔼可亲、对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捕的学生深怀同情的印捕的形象。
另一位左翼作家杨邨人在1929年的《大众文艺》发表题为《红头阿三》的文章,文中作者也一改之前对于印捕的负面态度,塑造了一个和蔼可亲、对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捕的学生深怀同情的印捕的形象。 这些故事都是典型的对于他者形象的建构,创作者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把印捕也纳入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的宏大叙事之中。他们天真地认为,印捕作为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印度人的代表,应当和他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知识分子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借助社会上负面形象代表的爱国行为来促进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分子惯用的宣传模式,诸如“青楼救国团”这样的组织屡见不鲜。
这些故事都是典型的对于他者形象的建构,创作者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把印捕也纳入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的宏大叙事之中。他们天真地认为,印捕作为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印度人的代表,应当和他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知识分子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借助社会上负面形象代表的爱国行为来促进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分子惯用的宣传模式,诸如“青楼救国团”这样的组织屡见不鲜。 但小偷、娼妓、帮会等社会群体的爱国热情,究竟有多少是基于功利的考虑,又有多少是基于真正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犹未可知,更不必说印捕的想法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的印捕和中国人一样都是受到压迫的对象,因而印捕也会对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产生同情,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对锡克族的印捕来说,他们觉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同胞们有时候甚至比英国人更可恨。
但小偷、娼妓、帮会等社会群体的爱国热情,究竟有多少是基于功利的考虑,又有多少是基于真正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犹未可知,更不必说印捕的想法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的印捕和中国人一样都是受到压迫的对象,因而印捕也会对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产生同情,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对锡克族的印捕来说,他们觉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同胞们有时候甚至比英国人更可恨。 但在中文语境里面,对印捕形象的误解仍然广泛存在。本文希望廓清的是,锡克族的印捕在上海从未出现过基于民族主义的反英运动,他们的罢工也和这些运动无关。
但在中文语境里面,对印捕形象的误解仍然广泛存在。本文希望廓清的是,锡克族的印捕在上海从未出现过基于民族主义的反英运动,他们的罢工也和这些运动无关。
作者:刘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天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