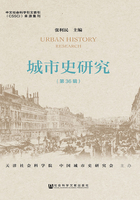
·区域体系与经济发展·
清代前期北京的粮食供给制度
内容提要:清代前期继承自明代的漕运制度,解决了刚进京的政府官员和八旗官兵的口粮问题。漕运是政府制定的一项经济制度,是政府集中行政力量进行的资源配置,也是京师粮食供给制度。实际上,清代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各时期政府并非固守制度不变,而是针对实际情况,欲对制度做一些变更,他们坚持的原则是因时制宜。只是改革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政府欲对漕运制度变革但没能成功。
关键词:清代前期 北京 粮食供给制度
制度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这里的制度是与粮食市场有关的具体制度,一般由政府 制定,自上而下实行。漕运是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即政府从南方一些省份征收粮食,然后利用运河或海运输往京城,供给政府官员、官兵及其家属消费。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关于漕运制度,前人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倪玉平总结了前人对漕运概念的界定,这里不再赘述。
制定,自上而下实行。漕运是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即政府从南方一些省份征收粮食,然后利用运河或海运输往京城,供给政府官员、官兵及其家属消费。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关于漕运制度,前人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倪玉平总结了前人对漕运概念的界定,这里不再赘述。 李文治、江太新指出:“漕运制度是在南北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京师需求大量粮食供应的条件下出现的。”
李文治、江太新指出:“漕运制度是在南北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京师需求大量粮食供应的条件下出现的。” 另外,还有于德源对北京漕运的专门研究。他提出:“北京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漕运始自东汉初年。”以后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中都,北京地区均有漕运供应的粮食。元、明两朝建都北京后,漕运制度中的仓储逐渐完善。“清朝继元、明之后定都北京,其京仓是在元、明旧物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由于自金朝以后,经北运河运到今北京(当时称中都)的漕粮都是经过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枢纽,然后转入通惠河(金称闸河)抵达京师,所以自金代就开始在京师内外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实际上都是京师太仓的一部分。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另外,还有于德源对北京漕运的专门研究。他提出:“北京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漕运始自东汉初年。”以后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中都,北京地区均有漕运供应的粮食。元、明两朝建都北京后,漕运制度中的仓储逐渐完善。“清朝继元、明之后定都北京,其京仓是在元、明旧物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由于自金朝以后,经北运河运到今北京(当时称中都)的漕粮都是经过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枢纽,然后转入通惠河(金称闸河)抵达京师,所以自金代就开始在京师内外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实际上都是京师太仓的一部分。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军队及其家属人员的口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清代政府继承明制,推行漕运制度,解决北京城市的粮食供给问题。漕运制度包括征收、运输、仓储等部分,与北京城市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是漕粮仓储和分配制度,本文主要探讨漕运制度中仓储一项。
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军队及其家属人员的口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清代政府继承明制,推行漕运制度,解决北京城市的粮食供给问题。漕运制度包括征收、运输、仓储等部分,与北京城市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是漕粮仓储和分配制度,本文主要探讨漕运制度中仓储一项。
一
对于京、通二仓的设立数量,于德源、李文治、李明珠 都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京、通二仓的不同,在于“通仓规模比一般京仓的规模要大,这是和通州作为漕粮入京转运枢纽的地位分不开的”。
都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京、通二仓的不同,在于“通仓规模比一般京仓的规模要大,这是和通州作为漕粮入京转运枢纽的地位分不开的”。 李明珠说,“尚未弄清京通二仓之间职能上的差异”;
李明珠说,“尚未弄清京通二仓之间职能上的差异”;  而于德源专述了清代京、通二仓的设官、职能等问题,指出二仓在这方面的不同,京、通二仓由户部云南司兼管,设总督仓场侍郎。仓场衙门下分设京粮厅和坐粮厅,各仓还有仓监督,均指派八旗官兵驻防,担负守卫之责。京、通二仓主要是支放官员的俸米和旗兵的甲米,所不同的是,二仓在分配、支领俸、甲米的变化。最初,因“北京至通州之间交通不便,漕粮转输困难,所以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都要到通仓支领俸甲米,自运回京”。后来通惠河水路畅通,“京仓储粮充足,于是王俸、官僚禄米石仍在通州支领,收入低薄的八旗兵丁的甲米则改在京仓就近支领”。乾隆五十九年(1794),规定“贵族、高官的资财雄厚,就仍令自出脚费,在通仓支领俸米”。嘉庆元年更改官员支领俸米例,“官员应领俸米”中“白粮概行划归,在通领米之王公大臣支领”,再“将王公大臣应领稉米,抵给文武各员”。
而于德源专述了清代京、通二仓的设官、职能等问题,指出二仓在这方面的不同,京、通二仓由户部云南司兼管,设总督仓场侍郎。仓场衙门下分设京粮厅和坐粮厅,各仓还有仓监督,均指派八旗官兵驻防,担负守卫之责。京、通二仓主要是支放官员的俸米和旗兵的甲米,所不同的是,二仓在分配、支领俸、甲米的变化。最初,因“北京至通州之间交通不便,漕粮转输困难,所以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都要到通仓支领俸甲米,自运回京”。后来通惠河水路畅通,“京仓储粮充足,于是王俸、官僚禄米石仍在通州支领,收入低薄的八旗兵丁的甲米则改在京仓就近支领”。乾隆五十九年(1794),规定“贵族、高官的资财雄厚,就仍令自出脚费,在通仓支领俸米”。嘉庆元年更改官员支领俸米例,“官员应领俸米”中“白粮概行划归,在通领米之王公大臣支领”,再“将王公大臣应领稉米,抵给文武各员”。
对漕粮运入京城的数量,法国学者魏丕信的研究指出:“从最大限度上讲,北京和通州每年预期可得到的漕粮数量等于各省缴纳的数额。星斌夫提供的康熙朝的总数是396.03万石(328.35万石运往北京,67.68万石运往通州)。欣顿(Hin-ton)(全汉昇和克劳斯引用了他的数字)提出,1829年为348.25万石。普莱费尔(Playfair)从《大清会典》中找到的1818年的数字相当低,总额为米2132959石,麦56724石,豆209423石。其他资料的说法各异,有400万石(清代最初的数额),3217024石(《大清会典》,1753年的数字),3205140石(《户部则例》,1851年?)。总的来看,对于18世纪来说,320万石这一数字看来是比较合理的。” 李文治提出:“顺治三年全国北运京师的漕粮约在90万石左右。”
李文治提出:“顺治三年全国北运京师的漕粮约在90万石左右。” 刘小萌指出,康熙二十四年(1685),实运289万石;雍正四年(1726),实运329万石。
刘小萌指出,康熙二十四年(1685),实运289万石;雍正四年(1726),实运329万石。 “嘉庆以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以上,或接近400万石。道光之后逐渐减少。”
“嘉庆以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以上,或接近400万石。道光之后逐渐减少。” 倪玉平也指出,漕粮征收量是不够的,乾隆十八年(1753)也只有352万余石。“其他绝大多数时间,全漕目标很难达到。”
倪玉平也指出,漕粮征收量是不够的,乾隆十八年(1753)也只有352万余石。“其他绝大多数时间,全漕目标很难达到。” 应该说,漕粮运至北京、通州的实际数字,各年是不一样的,以上学者的估算和看法也都有其依据。但是从京、通二仓储粮的角度看,漕粮的实际数量是足够供应京师的。
应该说,漕粮运至北京、通州的实际数字,各年是不一样的,以上学者的估算和看法也都有其依据。但是从京、通二仓储粮的角度看,漕粮的实际数量是足够供应京师的。
应该说,运粮量与仓储量不是一回事,每年漕粮运量并不一样,因为运粮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时征收不足额,或运输中损坏以致缺额,或者部分截留。不过漕粮运入京、通二仓后,经支放分配,还会有一些余剩,每次剩余粮续存在仓中,所以粮仓储量可能是逐渐增加的。粮仓能贮存的粮食量,与粮仓廒的个数有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总督仓场查罗沙赖等奏称:“京八仓廒座贮米已满。” 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和硕雍亲王疏言,运京仓之米,“通共五百六十二廒。又有院内露囤共十五围”。建议增建42廒。
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和硕雍亲王疏言,运京仓之米,“通共五百六十二廒。又有院内露囤共十五围”。建议增建42廒。 后来,雍正帝追忆,“先因京师米价腾贵,皇考宵旰焦劳,特命朕查视各仓。彼时见仓粮充溢,露积不少,因请将应行出仓之米,迅速办理”。当时命“监督张坦麟、陈守创等,会同仓场总督带领工部贤能司官,将仓廒确实料估,应修补者,速行修补。应添建者,于明岁春初添建。所需钱粮,动用捐贮驿站银两,其应否补项之处,再议”。
后来,雍正帝追忆,“先因京师米价腾贵,皇考宵旰焦劳,特命朕查视各仓。彼时见仓粮充溢,露积不少,因请将应行出仓之米,迅速办理”。当时命“监督张坦麟、陈守创等,会同仓场总督带领工部贤能司官,将仓廒确实料估,应修补者,速行修补。应添建者,于明岁春初添建。所需钱粮,动用捐贮驿站银两,其应否补项之处,再议”。 雍正时,政府认为,“京师人民聚集,食指浩繁,米粮关系重大,储备不可不多”。
雍正时,政府认为,“京师人民聚集,食指浩繁,米粮关系重大,储备不可不多”。 正是政府多贮漕粮,多建仓廒的措施,使得其间漕粮存储量不仅大,且新建了不少仓廒。四年(1726)十二月,仓场侍郎托时疏言,“今通州大西、中南两仓,存贮稄、粟米石,足支数十年,廒座不敷,新粮多系露囤”。他提出了改兑稄米、存贮京仓等解决办法。
正是政府多贮漕粮,多建仓廒的措施,使得其间漕粮存储量不仅大,且新建了不少仓廒。四年(1726)十二月,仓场侍郎托时疏言,“今通州大西、中南两仓,存贮稄、粟米石,足支数十年,廒座不敷,新粮多系露囤”。他提出了改兑稄米、存贮京仓等解决办法。 六年(1728)七月,总督仓场岳尔岱等奏称,“储畜 [蓄] 充盈,京仓廒座不敷,请添建以为收贮之地。”政府命工部相度地方,新建仓廒。七年(1729),巡视南城御史焦祈年奏内称,“各仓所贮米廒旧例每廒一万一千六百石,缘雍正六年到通粮多,廒座不敷,归并加添,所以有一万三四千及一万六千石不等”。
六年(1728)七月,总督仓场岳尔岱等奏称,“储畜 [蓄] 充盈,京仓廒座不敷,请添建以为收贮之地。”政府命工部相度地方,新建仓廒。七年(1729),巡视南城御史焦祈年奏内称,“各仓所贮米廒旧例每廒一万一千六百石,缘雍正六年到通粮多,廒座不敷,归并加添,所以有一万三四千及一万六千石不等”。 九年(1731),大学士蒋廷锡奏称:“京、通各仓共存历年漕白一千三百五十八万石,计每年进京、通仓正耗米四百余万石,除支放俸饷等项三百余万石,约可剩米一百余万石。今京通仓廒座俱充盈。”
九年(1731),大学士蒋廷锡奏称:“京、通各仓共存历年漕白一千三百五十八万石,计每年进京、通仓正耗米四百余万石,除支放俸饷等项三百余万石,约可剩米一百余万石。今京通仓廒座俱充盈。” “京仓之米足支五年。”
“京仓之米足支五年。” 至十一年(1733),“经仓场奏明,将存仓稄米发粜一百万石,节年粜卖十万余石,尚存未粜米八十余万石,均雍正三年以前陈积,其间多有气头廒底,亟需售粜”。
至十一年(1733),“经仓场奏明,将存仓稄米发粜一百万石,节年粜卖十万余石,尚存未粜米八十余万石,均雍正三年以前陈积,其间多有气头廒底,亟需售粜”。 乾隆时,政府仍然是多储粮,多建仓廒的做法。六年(1741)八月,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被批准。
乾隆时,政府仍然是多储粮,多建仓廒的做法。六年(1741)八月,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被批准。 后来英国使者到通州,见“城内有几个大粮仓储藏着各种粮食。据说永远储备着足够首都几年需用的粮食”。
后来英国使者到通州,见“城内有几个大粮仓储藏着各种粮食。据说永远储备着足够首都几年需用的粮食”。 到嘉庆时期,米粮储备更加富裕。四年(1799),据仓场侍郎称:“全漕到通每年积存米六十万石,积至嘉庆十四以后,京仓即可盈满。通仓现有廒二百五十座,计可贮米二百余万石。”
到嘉庆时期,米粮储备更加富裕。四年(1799),据仓场侍郎称:“全漕到通每年积存米六十万石,积至嘉庆十四以后,京仓即可盈满。通仓现有廒二百五十座,计可贮米二百余万石。” “节年均有轮免漕粮省分,是以到通漕米比之往年较少。然仓储并无不敷,至明岁以后,则全漕抵通,源源挽运,倍臻饶裕。”
“节年均有轮免漕粮省分,是以到通漕米比之往年较少。然仓储并无不敷,至明岁以后,则全漕抵通,源源挽运,倍臻饶裕。” 有学者统计,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嘉庆十七年(1812)的130年间,乾隆以前的54年,“增仓廒867座”。“三十六年裁通州20廒。”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庆十七年的41年间,修建了1000多廒,其中很难分清是建还是修,所以只能说是不断增廒的。同治四年(1865)才开始减廒。
有学者统计,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嘉庆十七年(1812)的130年间,乾隆以前的54年,“增仓廒867座”。“三十六年裁通州20廒。”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庆十七年的41年间,修建了1000多廒,其中很难分清是建还是修,所以只能说是不断增廒的。同治四年(1865)才开始减廒。 道光时期,虽然运到京城的漕粮比以前减少了,但仓储粮食量还是丰足的。十六年(1836)六月,御史万超奏称,“漕粮正额不足”。
道光时期,虽然运到京城的漕粮比以前减少了,但仓储粮食量还是丰足的。十六年(1836)六月,御史万超奏称,“漕粮正额不足”。 而铁麟等奏称,“朝阳门外太平、储济、万安、裕丰四仓,现贮米石较之城内七仓,多至一两倍。新粮抵通,难于照例拨派。”后决定:“所有道光十五年秋季、十六年春季,八旗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官员俸米,准其援照旧案,改由城外四仓支放。”“八旗甲米,于外四仓应行轮放之外,接续多放两轮。俾得疏通旧贮,即可拨进新漕,以速转运而利回空。”
而铁麟等奏称,“朝阳门外太平、储济、万安、裕丰四仓,现贮米石较之城内七仓,多至一两倍。新粮抵通,难于照例拨派。”后决定:“所有道光十五年秋季、十六年春季,八旗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官员俸米,准其援照旧案,改由城外四仓支放。”“八旗甲米,于外四仓应行轮放之外,接续多放两轮。俾得疏通旧贮,即可拨进新漕,以速转运而利回空。” 从中也透漏出满仓的信息。另据魏丕信的研究,“有时由于粮食源源不断地到达,而京城和周边地区的粮食需求相对不足,即粮食供大于求,造成运河北端地区仓储设施的紧张”。
从中也透漏出满仓的信息。另据魏丕信的研究,“有时由于粮食源源不断地到达,而京城和周边地区的粮食需求相对不足,即粮食供大于求,造成运河北端地区仓储设施的紧张”。 李文治也指出,通州各仓积贮粮“清初至乾隆为前期,存粮最多;嘉庆、道光两朝为中期,积存渐少,然仍能支应”。
李文治也指出,通州各仓积贮粮“清初至乾隆为前期,存粮最多;嘉庆、道光两朝为中期,积存渐少,然仍能支应”。 李明珠亦有同样的观点。
李明珠亦有同样的观点。 可见,京、通仓储存粮食的数量比较多,且足够京城人食用多年。
可见,京、通仓储存粮食的数量比较多,且足够京城人食用多年。
由于储存粮爆满,政府开始考虑暂停漕运的变革。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康熙帝问大学士京师粮米储存有多少。他说:“思完纳漕粮一项,小民良苦,亦欲特赐蠲征,此念已久。”令大臣对此议奏。 大学士等回复:“确查米数,现今仓内储米七百八十万石有奇,足供三年给放。”康熙帝称欲蠲免30年漕粮。大臣们奏称,“京师根本重地,漕粮输挽关系国计,似难轻议全蠲。况五方杂处,人烟凑集,需用孔多,若一年停运,米既不能北来,百货价值亦将腾贵。”或者可以各省轮免二三年。康熙帝称:“朕急思轸恤民生,于都城人民食用之需,未曾计及。”就此同意大臣的意见,没有蠲免漕粮。
大学士等回复:“确查米数,现今仓内储米七百八十万石有奇,足供三年给放。”康熙帝称欲蠲免30年漕粮。大臣们奏称,“京师根本重地,漕粮输挽关系国计,似难轻议全蠲。况五方杂处,人烟凑集,需用孔多,若一年停运,米既不能北来,百货价值亦将腾贵。”或者可以各省轮免二三年。康熙帝称:“朕急思轸恤民生,于都城人民食用之需,未曾计及。”就此同意大臣的意见,没有蠲免漕粮。 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有意改变漕运的制度。
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有意改变漕运的制度。
雍正时,政府“念京通各仓积贮丰裕,欲纾输将之力,恤挽运之劳。又欲民间受折征之益,弁丁无停运之累,以岁运漕粮作何变通之处,行令漕臣筹划”。 实际是雍正帝看到“京仓之米足支五年,是以敕议折征”。“议停各省漕运。”当时“密咨南北抚臣,并行布政司粮道议复”。“将正耗米石全以每石七钱折征。其漕船仍给岁修,量留旗丁水手数名看守,该丁等酌给口粮,运弁亦给养廉,俾无停运之累。”时任漕运总督的性桂提出不同意见,他曾任巡城御史,知道京城“万方辏集,食指繁多,运丁之有余耗者,可以粜济民食,倘或全停,米价恐贵,若以通仓两年之余米,平价出粜,似不必令民折征,而仓储可免红腐之虞矣”。
实际是雍正帝看到“京仓之米足支五年,是以敕议折征”。“议停各省漕运。”当时“密咨南北抚臣,并行布政司粮道议复”。“将正耗米石全以每石七钱折征。其漕船仍给岁修,量留旗丁水手数名看守,该丁等酌给口粮,运弁亦给养廉,俾无停运之累。”时任漕运总督的性桂提出不同意见,他曾任巡城御史,知道京城“万方辏集,食指繁多,运丁之有余耗者,可以粜济民食,倘或全停,米价恐贵,若以通仓两年之余米,平价出粜,似不必令民折征,而仓储可免红腐之虞矣”。 江西巡抚谢旻也奏称:“南北货物多于粮船带运,京师借以利用,关税借以充足,而沿途居民借此为生理者亦复不少。若一停运,则虽有行商贩卖贸迁,未必能多,货物必致阻滞,关税亦恐不无缺少。”
江西巡抚谢旻也奏称:“南北货物多于粮船带运,京师借以利用,关税借以充足,而沿途居民借此为生理者亦复不少。若一停运,则虽有行商贩卖贸迁,未必能多,货物必致阻滞,关税亦恐不无缺少。” 总结他们反对的理由如下:首先,怕漕船朽坏不可用。若将来复粮运,船不能使用。其次,若漕运停止,以此为生的民众会失业。再次,如果全征折色,大批原粮在民间销售,谷价贱,则伤农。最后,京城需要漕粮,否则米价上涨,百货昂贵。因为是密折奏报,所以笔者能看到的奏折不多,估计大多数官员都是反对的,所以这次漕粮折征之议没能推行。
总结他们反对的理由如下:首先,怕漕船朽坏不可用。若将来复粮运,船不能使用。其次,若漕运停止,以此为生的民众会失业。再次,如果全征折色,大批原粮在民间销售,谷价贱,则伤农。最后,京城需要漕粮,否则米价上涨,百货昂贵。因为是密折奏报,所以笔者能看到的奏折不多,估计大多数官员都是反对的,所以这次漕粮折征之议没能推行。
嘉庆时,铁保等人提出将俸、甲米“十成中,酌折二成银两”发放的意见,嘉庆帝“觉其事窒碍难行,特以集思广益,不厌精详”。“不妨据实直陈,以备采择。”户部、八旗满洲都统、仓场侍郎等均各抒己见,似乎未见支持的意见。他们说:“京师五方辐辏,商民云集,本处产粮既少,又无别项贩运粮石,专赖官员、兵丁等所余之米,流通粜籴,借资糊口。”如果“改给折色二成,不惟于八旗生计,恐致拮据,即以每岁少放米五十余万石计算,于商民口食之需,亦多未便”。改折发放,不但市场上的粮食少了,而且仓储中的粮食也会陈陈相因。 铁保提出了漕粮折征发放的意见,实际也是对原有漕粮分配制度的改革,但最终被否定。
铁保提出了漕粮折征发放的意见,实际也是对原有漕粮分配制度的改革,但最终被否定。
二
清代前期政府继承明代的漕运制度,供给京城漕粮。漕运制度本身有许多弊端,且因延续时间长久,特别是在执行中弊病更多。这些弊病早在明代就存在,清代前期并未见有多少改变。由于前人专门对清代漕运制度进行了全面研究,还有学者对其中与京城有关的部分,即最后的运输、存储阶段的弊端,有详细探讨, 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专门对仓储支放漕粮方面的制度弊病,引用清前期京城的具体资料和案例,进行简要梳理。
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专门对仓储支放漕粮方面的制度弊病,引用清前期京城的具体资料和案例,进行简要梳理。
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官、吏、商相互勾结,贪占漕粮。
雍正时,刘康时在中城居住,任工部灰户,即政府雇用商人。其“包揽京、通十一仓工程”,“先后领五万两银”。后来工部奏报,工料已领,只剩4000余两,但工程完成尚不及1/10。虽然刘康时不承认与人瓜分银两,但表示以后不再领款项,变卖家产也要完成工程。 估计其中必有问题。且雇用刘康时的总督李瑛贵也有贪污问题。有人揭发,“访得国柱系总督李瑛贵派委侵夺坐粮厅职掌一切,验米起卸不由满汉坐粮厅作主,国柱从中掣肘,每船分外需索旗丁使费银二三两不等,以致起卸迟延”。李瑛贵“令经纪宛君甫、张公玉”等人“包揽科派,在大通桥现立官柜,每船旗丁另派钱三千余文”。
估计其中必有问题。且雇用刘康时的总督李瑛贵也有贪污问题。有人揭发,“访得国柱系总督李瑛贵派委侵夺坐粮厅职掌一切,验米起卸不由满汉坐粮厅作主,国柱从中掣肘,每船分外需索旗丁使费银二三两不等,以致起卸迟延”。李瑛贵“令经纪宛君甫、张公玉”等人“包揽科派,在大通桥现立官柜,每船旗丁另派钱三千余文”。 另据经纪宛君甫等人供述,“今年六月内,不记得日期,总督李瑛贵将我们经纪传到他家,向我们商议运粮进仓,要节省二万钱粮之事”。侯国柱出主意说:“你们经纪头目十人,在大通桥设局立柜,分作两班,轮流居住,将各经纪所要旗丁的钱收来,运米进仓交了钱的旗丁米虽些须差些,将就收了罢,仓内用的两吊八百钱是少不得的。”于是经纪头目“在大通桥设局,立柜收钱。除每船要仓买钱两吊八百文外,又要钱一千二百余文,以备柜人盘费之用。”“每船看米多寡要钱,四千、三千、二千不等。”并由家人张四向经纪收八十千钱,送到总督李家。
另据经纪宛君甫等人供述,“今年六月内,不记得日期,总督李瑛贵将我们经纪传到他家,向我们商议运粮进仓,要节省二万钱粮之事”。侯国柱出主意说:“你们经纪头目十人,在大通桥设局立柜,分作两班,轮流居住,将各经纪所要旗丁的钱收来,运米进仓交了钱的旗丁米虽些须差些,将就收了罢,仓内用的两吊八百钱是少不得的。”于是经纪头目“在大通桥设局,立柜收钱。除每船要仓买钱两吊八百文外,又要钱一千二百余文,以备柜人盘费之用。”“每船看米多寡要钱,四千、三千、二千不等。”并由家人张四向经纪收八十千钱,送到总督李家。 后来又揭发,仓役利用没有详细规定粳、稄、粟各米色的具体数量,而提出“米色不同,价值亦异”。“每有不肖仓役,勾通拨什库等役,从中贾利,以粟易稄,以稄易稉 [粳],互相分肥,成为通弊,竟相沿有换色之名,牢不可破。”
后来又揭发,仓役利用没有详细规定粳、稄、粟各米色的具体数量,而提出“米色不同,价值亦异”。“每有不肖仓役,勾通拨什库等役,从中贾利,以粟易稄,以稄易稉 [粳],互相分肥,成为通弊,竟相沿有换色之名,牢不可破。”
乾隆十九年(1764),步军统领阿里衮奏称:“有奸民包揽打米,内外勾通,每石勒取钱一二百之多。”其中北新仓“监督德昌家人韩八,串通搂包花户祁盛等”人,“包揽打米四百余石,每石索取制钱五十文”。据北新仓监督刑部主事德昌家人韩八供述,“五月十八日有认识的祁盛,向小的说有包衣甲米四百八十三石,烦小的替他仓内照应,打些好米,每石给使用钱八十文,小的应允”。祁盛供述:“系大兴县人,因无营业,每逢开仓放米,小的同伙计李五、王二、闫大、曹三,替旗人包卖些米,每石希图赚钱一二十文,大家分使。”车夫刘老儿供述:“五月十八日,有正黄旗包衣披甲人来生单四,雇小的车在北新仓拉米,叫小的托人替他打好米,除脚价外,讲定每石使用廒钱一百文,小的就向搂包人祁盛说明,替来生打了老米一百三十石,单四打了老米七十三石,他二人给了廒用钱二十吊零三百文,小的给了祁盛钱十七吊。” “铺户包揽旗员俸米,兵丁甲米,与仓书、斗级,私自交结,赴仓支领,希图从中取利,其弊由来已久。”
“铺户包揽旗员俸米,兵丁甲米,与仓书、斗级,私自交结,赴仓支领,希图从中取利,其弊由来已久。”
嘉庆时,自漕粮“抵坝贮仓以后,该仓场侍郎以及监督等官,均不知慎重职守,历任相沿,因循废弛,怠忽疲玩,遂至搀 [掺] 和,抵窃百弊丛生”。 御史余本敦参奏裕丰仓监督,“开仓后,辄自回家。封条交与花户封贴”。给花户等乘间舞弊的机会。
御史余本敦参奏裕丰仓监督,“开仓后,辄自回家。封条交与花户封贴”。给花户等乘间舞弊的机会。 大兴县人赵维屏在东直门外菜市开设商铺,从八年(1803)至十年(1805)在海运仓充当挖勺头目。他与“定亲王府太监庄姓并春李结盟”,“与东城副指挥周连相好”。如“遇有打官司的人”,他可去托个人情。“每逢放米时,将廒内米石挖出,打做天堆,将好米堆在一面,次米堆在一面。有要吃好米的人,每石索要使费钱九十文。”
大兴县人赵维屏在东直门外菜市开设商铺,从八年(1803)至十年(1805)在海运仓充当挖勺头目。他与“定亲王府太监庄姓并春李结盟”,“与东城副指挥周连相好”。如“遇有打官司的人”,他可去托个人情。“每逢放米时,将廒内米石挖出,打做天堆,将好米堆在一面,次米堆在一面。有要吃好米的人,每石索要使费钱九十文。” 十六年(1811),“中城副指挥孔传葵,于该城米厂粜毕封仓后,擅自揭去封条,将稉 [粳] 米装载二十五石,拉至署内交卸后,复又至厂照数装运”。
十六年(1811),“中城副指挥孔传葵,于该城米厂粜毕封仓后,擅自揭去封条,将稉 [粳] 米装载二十五石,拉至署内交卸后,复又至厂照数装运”。
以下是一个发生在嘉庆年间的典型案例。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福庆、许兆椿密奏,“通州中、西二仓所贮白米多有亏缺,并查有积蠹高添凤私用花押白票装米出仓,兼令伊弟高二桂名大班番子以为护符”。后经托津等官员调查,“西仓地字廒短少白米七百余石,中仓法字廒短少白米四百余石。此外廒座尚多,即分起抽丈,与原贮数目多有不符,约计一廒或短百余石、数百石,及千余石不等,米色亦多不纯,其中间有霉变”。 官员将高添凤等人抓捕,审问得知,通州人高添凤,原充任海运仓书吏,役满后于嘉庆三年(1798)由其弟高凤鸣充当西仓甲斗头役,至八年役满,高添凤的儿子高廷柱接充,至十三年(1808)役满,又叫其表弟赵长安接充。这十余年间,仓中事务实际由高添凤一人办理。他供称:“仓里每年约进白米四万余石,定例总是先尽陈米开放,斛面微凹,放完后才能合数。”十年十一月,“因有应运京土米一万石,我止领出土米八千四百石,私自掉 [调] 换廒座,顶出白米一千六百石售卖,共得京钱七千余吊”。“白米到仓,原是书吏潘章经管,向来旗丁讲究使费,每船京钱二三十吊至五六十吊不等,就可包含米色斛面,每石少收二三升。每船一只,潘章只分给我京钱二吊四百五十文。”于是,他每次“向领米人每石索钱二三百至四五百文不等,放给好米并满量斛面,每石约多出米二三千。后来陈米渐多,只得偷换廒座支放”。十一年(1806)春季,高添凤与潘章商量,“私出白米三百石,卖得京钱一千八百吊”。他“叫攒典陈瑞亭、康连茹将放过米票不即销号,重领出来的,名为黑档”。十三年春季,他与“宋均、赵鹤龄商允多开廒票,私出米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秋季又私出米五百零二石。”十四年“春季又私出米五百二十石”。总计,高添凤在“仓十余年”,采取少收多出的办法,送内务府白米,二尖斛外加四升,后加至四大升;麻袋宽每石多装数升至斗余不等,“每年运米四千余石,其多出米数又不下四百余石”。有相关花户、人役、书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二年,充当中仓甲斗头役的通州人张连芳,有米局人收买俸票,到仓领米时,他每石索要钱二三百或四五百文不等,才放给新米,而每石多出米二三升不等。他说:“承办十余年来都是如此,约每年多出米四五百石。”四年(1799)充当西仓花户鲁五承办运送内务府白米。“自十年起到今年春间止,共得过米三千余石。”“每年白粮帮船共八十余只,每船交米四五百石不等。”九年充当西仓书吏潘章,需索旗丁京钱一千余吊,少收斛面。又收高添凤贿赂京钱四百吊,听任其私出黑档。十年充当西仓攒典宋均专门负责开假票私出米。
官员将高添凤等人抓捕,审问得知,通州人高添凤,原充任海运仓书吏,役满后于嘉庆三年(1798)由其弟高凤鸣充当西仓甲斗头役,至八年役满,高添凤的儿子高廷柱接充,至十三年(1808)役满,又叫其表弟赵长安接充。这十余年间,仓中事务实际由高添凤一人办理。他供称:“仓里每年约进白米四万余石,定例总是先尽陈米开放,斛面微凹,放完后才能合数。”十年十一月,“因有应运京土米一万石,我止领出土米八千四百石,私自掉 [调] 换廒座,顶出白米一千六百石售卖,共得京钱七千余吊”。“白米到仓,原是书吏潘章经管,向来旗丁讲究使费,每船京钱二三十吊至五六十吊不等,就可包含米色斛面,每石少收二三升。每船一只,潘章只分给我京钱二吊四百五十文。”于是,他每次“向领米人每石索钱二三百至四五百文不等,放给好米并满量斛面,每石约多出米二三千。后来陈米渐多,只得偷换廒座支放”。十一年(1806)春季,高添凤与潘章商量,“私出白米三百石,卖得京钱一千八百吊”。他“叫攒典陈瑞亭、康连茹将放过米票不即销号,重领出来的,名为黑档”。十三年春季,他与“宋均、赵鹤龄商允多开廒票,私出米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秋季又私出米五百零二石。”十四年“春季又私出米五百二十石”。总计,高添凤在“仓十余年”,采取少收多出的办法,送内务府白米,二尖斛外加四升,后加至四大升;麻袋宽每石多装数升至斗余不等,“每年运米四千余石,其多出米数又不下四百余石”。有相关花户、人役、书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二年,充当中仓甲斗头役的通州人张连芳,有米局人收买俸票,到仓领米时,他每石索要钱二三百或四五百文不等,才放给新米,而每石多出米二三升不等。他说:“承办十余年来都是如此,约每年多出米四五百石。”四年(1799)充当西仓花户鲁五承办运送内务府白米。“自十年起到今年春间止,共得过米三千余石。”“每年白粮帮船共八十余只,每船交米四五百石不等。”九年充当西仓书吏潘章,需索旗丁京钱一千余吊,少收斛面。又收高添凤贿赂京钱四百吊,听任其私出黑档。十年充当西仓攒典宋均专门负责开假票私出米。 后来官员总结称,“此案已满仓书高添凤、甲斗张连芳,盘踞西中二仓,私出斛面黑档,亏短白米十余万石,肆行无忌,实为从来未有之事。攒典宋均听从高添凤私出黑档,分用钱文二千四百余吊,赃数较多”。而“监督德楞额、玉通,听信家人怂恿,德楞额三次得受宋均京钱一千七百吊,玉通得受宋均京钱八百吊。又得受潘章京钱三百吊,遂任伊等在仓舞弊,于法实有所枉”。
后来官员总结称,“此案已满仓书高添凤、甲斗张连芳,盘踞西中二仓,私出斛面黑档,亏短白米十余万石,肆行无忌,实为从来未有之事。攒典宋均听从高添凤私出黑档,分用钱文二千四百余吊,赃数较多”。而“监督德楞额、玉通,听信家人怂恿,德楞额三次得受宋均京钱一千七百吊,玉通得受宋均京钱八百吊。又得受潘章京钱三百吊,遂任伊等在仓舞弊,于法实有所枉”。 据官员奏报,本来步军统领衙门设立番役,是为了“稽查缉捕”,但是他们与“花户、库丁、炉头等挂名互充”的吏役,相互勾结。当发现“花户高添凤等侵盗通仓米石”时,官员禄康派令“番役前往访拿。该番役不但不肯指拿到案,直云并无高姓其人”。后得知,高添凤之弟高二,“现充番役”,特“恃为护符。”在查抄高添凤家产时,发现了镶玉如意。据审问得知,这是番役马凯送高添凤“母祝寿之物”。可见他们“平日之固结交好,串通舞弊情形显而易见”。
据官员奏报,本来步军统领衙门设立番役,是为了“稽查缉捕”,但是他们与“花户、库丁、炉头等挂名互充”的吏役,相互勾结。当发现“花户高添凤等侵盗通仓米石”时,官员禄康派令“番役前往访拿。该番役不但不肯指拿到案,直云并无高姓其人”。后得知,高添凤之弟高二,“现充番役”,特“恃为护符。”在查抄高添凤家产时,发现了镶玉如意。据审问得知,这是番役马凯送高添凤“母祝寿之物”。可见他们“平日之固结交好,串通舞弊情形显而易见”。
在案件中,还揭发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与书吏、人役等人勾结,从中获利的情况。据官员奏报,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自行交代,礼亲王昭槤从嘉庆十一年起,共在通州卖米票五次。睿亲王端恩、豫亲王裕丰、肃亲王永锡、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定亲王绵恩、顺承郡王伦柱、克勤郡王尚格、庆郡王永璘、贝勒永珠、贝勒绵懃、贝勒奕纶、贝勒奕绮、贝子奕绍“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和郡王绵偱“历年余剩俸米俱卖与东四牌楼(北十一条胡同西口外路东)孙姓广聚米局,及白庙(北路西)纪姓增盛(店)碓房”。荣郡王绵亿“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卖与灯市口义合米局吴姓自行运京”。怡亲王奕勋“每年应领俸米俱由通仓照票关领,除本门上食用米石外,其余剩零米卖给通州德和米局。高添凤供历年承买米票”。贝勒绵誉十四年“春季在通州卖票一次”。贝勒绵志“历年均在通州照票领米,除本门上留用米石之外,余俱在通州米局售卖”。“惟本年春季本门上参领伦常保卖票一次。” 尽管这些皇亲国戚出卖米票,不是都卖给高添凤,但是高添凤在嘉庆四年,“开设天增钱铺”。
尽管这些皇亲国戚出卖米票,不是都卖给高添凤,但是高添凤在嘉庆四年,“开设天增钱铺”。 又与山东福山县人刘大,“在灯市口伙开天得兴米铺一座”。
又与山东福山县人刘大,“在灯市口伙开天得兴米铺一座”。 九年,与通州生员曹文炯合伙“开德和米店”。“收买各官俸票赴仓领米,粜卖赚钱使用。”
九年,与通州生员曹文炯合伙“开德和米店”。“收买各官俸票赴仓领米,粜卖赚钱使用。” 高肯定收买了各官员大量米粮,据大学士董浩奏称,高添凤“买礼亲王米票五次,系在海姓、王姓、庆姓、和姓等手内承买”。
高肯定收买了各官员大量米粮,据大学士董浩奏称,高添凤“买礼亲王米票五次,系在海姓、王姓、庆姓、和姓等手内承买”。 高添凤的天增钱铺,“曾陆续收买王、贝勒及各官米票”。他拿米票到仓领新米,每次量米时,都要“多出斛面,约计每年春秋二季多出米五六百石”。
高添凤的天增钱铺,“曾陆续收买王、贝勒及各官米票”。他拿米票到仓领新米,每次量米时,都要“多出斛面,约计每年春秋二季多出米五六百石”。 最后,政府定案称:“此案已满仓书高添凤、甲斗张连芳,盘踞西中二仓,私出斛面黑档,亏短白米十余万石,肆行无忌,实为从来未有之事。攒典宋均听从高添凤私出黑档,分用钱文二千四百余吊,赃数较多。”“仓书潘章需索旗丁使费京钱一千余吊,少收斛面,又得受高添凤京钱四百吊,听其私出黑档,情节较重。”
最后,政府定案称:“此案已满仓书高添凤、甲斗张连芳,盘踞西中二仓,私出斛面黑档,亏短白米十余万石,肆行无忌,实为从来未有之事。攒典宋均听从高添凤私出黑档,分用钱文二千四百余吊,赃数较多。”“仓书潘章需索旗丁使费京钱一千余吊,少收斛面,又得受高添凤京钱四百吊,听其私出黑档,情节较重。”
制度弊端之二,各层次的制度参与者,都利用手中权力,盗卖仓米。
盗卖仓米是他们贪污漕粮的主要手段。这不仅早已存在,且始终未停止。顺治时,政府重申“各仓发米时,挨次支领,如有车辆拥挤,及偷盗等事,拿送刑部治罪”。 并且有专门法律条例规定:“偷盗米石例,从重治罪。”
并且有专门法律条例规定:“偷盗米石例,从重治罪。” 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漕粮由大通桥运进京仓,有拦路戳袋偷抢米者;有夜间挖墙偷米者;有越墙进仓偷米者”。
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漕粮由大通桥运进京仓,有拦路戳袋偷抢米者;有夜间挖墙偷米者;有越墙进仓偷米者”。 五十五年(1716),“通州中南仓长于德瑞盗白米一百六十石,交付民人冯二,卖给宣武门外米铺民人吴昭齐”。于德瑞让在通州开当铺之浙江人沈三,代“其拟写发帖售米”。沈三从中每石得银二钱。冯二是卖米经纪人,每石得制钱20钱。冯二拿样米和沈三的售米发帖,到宣武门外吴昭齐米铺,与吴昭齐“议定每石一两三钱。于八月初六日,卖二百石白米,沈三亲取银两以去”。九月“初一日,冯二又送来米一百石。初五日,送来此六十石米,卸米时被俘”。
五十五年(1716),“通州中南仓长于德瑞盗白米一百六十石,交付民人冯二,卖给宣武门外米铺民人吴昭齐”。于德瑞让在通州开当铺之浙江人沈三,代“其拟写发帖售米”。沈三从中每石得银二钱。冯二是卖米经纪人,每石得制钱20钱。冯二拿样米和沈三的售米发帖,到宣武门外吴昭齐米铺,与吴昭齐“议定每石一两三钱。于八月初六日,卖二百石白米,沈三亲取银两以去”。九月“初一日,冯二又送来米一百石。初五日,送来此六十石米,卸米时被俘”。 另“坐粮厅经纪张永隆属下押米大役李玉,普济闸撑船甲长陈二、薛回子、白四、刘大、王大、杨九等合伙盗米下船,各送回家之时”被官兵尾随拿获。他们“于普济闸地方陆续偷盗,自通州运至大通桥之老米一百六十九石五斗”。
另“坐粮厅经纪张永隆属下押米大役李玉,普济闸撑船甲长陈二、薛回子、白四、刘大、王大、杨九等合伙盗米下船,各送回家之时”被官兵尾随拿获。他们“于普济闸地方陆续偷盗,自通州运至大通桥之老米一百六十九石五斗”。
雍正二年(1724),通州民朱黑子和孙文德,于四月初二日黄昏时,“从大西仓北门西边,跳墙进去,意欲夜间乘空偷米出来”。被查获。他们供称:“做贼有十几年了,也偷过好几次,年久记不清了。” 七年(1729)五月,雍正帝指出,“运丁人等繁多,素有恶习,如偷盗米石,挂欠官粮,夹带私货,藐视法纪,此向来之通弊也”。
七年(1729)五月,雍正帝指出,“运丁人等繁多,素有恶习,如偷盗米石,挂欠官粮,夹带私货,藐视法纪,此向来之通弊也”。
乾隆时重新对偷盗米石定例, 说明盗窃漕粮之事增多。四十二年(1777)八月,发生“通州船户梁天成盗卖漕米”案。剥船船户刘胜“伙同商谋之张士雄、薛天福”,“起意商同凿漏船底,偷盗米石”。
说明盗窃漕粮之事增多。四十二年(1777)八月,发生“通州船户梁天成盗卖漕米”案。剥船船户刘胜“伙同商谋之张士雄、薛天福”,“起意商同凿漏船底,偷盗米石”。 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发生“通州普济闸船户车喜儿”和“柏大、王大、杨六、季六、薛七”等人,“偷窃运送漕米”。“巡役韩连升、宛宁,知情容隐,复拒捕伤差。”“户车喜儿等,发往乌噜木齐,俱给兵丁为奴。”“韩连升、宛宁身充巡役,于船户等偷窃漕米,既未先时查拿,及被顺天府役盘获。该差等复纠众抢夺米驮,拒伤府役,希图掩饰,情罪可恶。韩连升虽属首犯,例应拟绞,业经身故。其宛宁一犯,亦系拒捕伤差造意之犯,未便任其诿卸死者,致令幸免。宛宁,著改为应绞监候。”
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发生“通州普济闸船户车喜儿”和“柏大、王大、杨六、季六、薛七”等人,“偷窃运送漕米”。“巡役韩连升、宛宁,知情容隐,复拒捕伤差。”“户车喜儿等,发往乌噜木齐,俱给兵丁为奴。”“韩连升、宛宁身充巡役,于船户等偷窃漕米,既未先时查拿,及被顺天府役盘获。该差等复纠众抢夺米驮,拒伤府役,希图掩饰,情罪可恶。韩连升虽属首犯,例应拟绞,业经身故。其宛宁一犯,亦系拒捕伤差造意之犯,未便任其诿卸死者,致令幸免。宛宁,著改为应绞监候。”
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有偷盗漕米王二、马大、杨大三人,他们称:“伊等俱系官船雇觅水手,每日装送米石至大通桥交卸。”每当“夜间将米袋打开,每袋偷出米二三升,或一二升不等,随时吃用,所剩止有七石有零。”这样偷盗已经“两月有余”。 同月,还发现有大兴县人张十、韩二等,在“东便门外二闸地方居住”,依靠“扛粮度日”。他们每日零星偷盗升斗米。
同月,还发现有大兴县人张十、韩二等,在“东便门外二闸地方居住”,依靠“扛粮度日”。他们每日零星偷盗升斗米。 十二月,大兴县人罗三、刘三、郑八十等,均“在朝阳门外二闸地方居住”。他们被官方雇用,或做粮船上的水手;或是在粮船上撑船。他们有机会陆续偷盗粮船上的米,共四石之多。
十二月,大兴县人罗三、刘三、郑八十等,均“在朝阳门外二闸地方居住”。他们被官方雇用,或做粮船上的水手;或是在粮船上撑船。他们有机会陆续偷盗粮船上的米,共四石之多。 同月,在禄米仓附近居住的正蓝旗汉军凌贵,伙同正白旗蒙古养育兵等,“偷出老米两半口袋,卖与开米铺之赵二,得钱五吊四百文分用。又于十四日夜,该犯等四人,仍旧爬墙进内,偷出老米四半口袋,卖与开米铺之王大,得钱十吊九百文分用”。
同月,在禄米仓附近居住的正蓝旗汉军凌贵,伙同正白旗蒙古养育兵等,“偷出老米两半口袋,卖与开米铺之赵二,得钱五吊四百文分用。又于十四日夜,该犯等四人,仍旧爬墙进内,偷出老米四半口袋,卖与开米铺之王大,得钱十吊九百文分用”。 直隶饶阳县人王四“在关家坟孟大菜园居住,捡粪度日”。束鹿县人张三“来京在大有庄北边居住,种菜园度日”。他们共同偷盗丰益仓米。
直隶饶阳县人王四“在关家坟孟大菜园居住,捡粪度日”。束鹿县人张三“来京在大有庄北边居住,种菜园度日”。他们共同偷盗丰益仓米。 又有保定府人王二,“在京推粪为生”。他在六年至八年的三年间,偷盗丰益仓米售卖。“六年十一月内偷窃丰益仓号房内稄米八斗,卖给添顺字号粮食店。”“七年二月内,又偷窃老米八斗,亦卖给添顺粮食店。”三月“偷窃老米两半口袋”,“亦卖给添顺粮食店”。
又有保定府人王二,“在京推粪为生”。他在六年至八年的三年间,偷盗丰益仓米售卖。“六年十一月内偷窃丰益仓号房内稄米八斗,卖给添顺字号粮食店。”“七年二月内,又偷窃老米八斗,亦卖给添顺粮食店。”三月“偷窃老米两半口袋”,“亦卖给添顺粮食店”。 同时,还发现有偷盗万安仓米贼,在“齐化门外大街,有窃贼拉运老米三石”。
同时,还发现有偷盗万安仓米贼,在“齐化门外大街,有窃贼拉运老米三石”。 十一年,大兴县人孟大等四人,在高碑店居住。他伙同兄弟“在粮船上陆续偷得稄米共有九石多”。
十一年,大兴县人孟大等四人,在高碑店居住。他伙同兄弟“在粮船上陆续偷得稄米共有九石多”。 十五年(1810),漕船额外余米经商人贩运,又回到漕船上的情况较多,“商贩运米石,先串通经纪,假立发票,票内开写由某处运至某处,以掩盖其出境之迹。实则联车运载囤积乡村,赴天津一带售与漕船”。“各仓侵偷米石,借以消售,以致漕船得有弥补,遂有恃而兑运不足。”
十五年(1810),漕船额外余米经商人贩运,又回到漕船上的情况较多,“商贩运米石,先串通经纪,假立发票,票内开写由某处运至某处,以掩盖其出境之迹。实则联车运载囤积乡村,赴天津一带售与漕船”。“各仓侵偷米石,借以消售,以致漕船得有弥补,遂有恃而兑运不足。” 十六年二月,“通仓向有钓扇偷米情弊”。“本月十二日,因查验各廒见重字白粮廒门板片脱落,形迹可疑。”官兵拿获偷米人耿狗儿等人。他们分别在十二、十三、十四日等,偷米四次。分别“卖给牛市东边饼子铺”和“南关刘痂子店”。
十六年二月,“通仓向有钓扇偷米情弊”。“本月十二日,因查验各廒见重字白粮廒门板片脱落,形迹可疑。”官兵拿获偷米人耿狗儿等人。他们分别在十二、十三、十四日等,偷米四次。分别“卖给牛市东边饼子铺”和“南关刘痂子店”。 五月,太平仓和万安仓“有钓扇偷米情事”。
五月,太平仓和万安仓“有钓扇偷米情事”。 七月,谷大伙同广渠门汛守兵张泳升等人,“偷窃裕丰仓米石”。“又向拉运号粮之金大车上戳袋偷米,金大得钱纵窃。”从金大车上“约共偷稄米三石零”。以后他们又联合起来从裕丰仓后墙“进仓,在新收廒座内,偷得稄米一石零”。另先后“偷得稄米两半口袋”;“稄米三半口袋”。“共偷得仓内稄米五石零。”后“谷大在东便门号房陆续偷得粳米一石零。”家住“东便门外蓝靛村”的陈三、李九等民人,也参与偷米,他们偷得稄米一石零。
七月,谷大伙同广渠门汛守兵张泳升等人,“偷窃裕丰仓米石”。“又向拉运号粮之金大车上戳袋偷米,金大得钱纵窃。”从金大车上“约共偷稄米三石零”。以后他们又联合起来从裕丰仓后墙“进仓,在新收廒座内,偷得稄米一石零”。另先后“偷得稄米两半口袋”;“稄米三半口袋”。“共偷得仓内稄米五石零。”后“谷大在东便门号房陆续偷得粳米一石零。”家住“东便门外蓝靛村”的陈三、李九等民人,也参与偷米,他们偷得稄米一石零。 八月,驾漕运船的卢大等八人,“在齐化门号里偷得官口袋七条,又同萧大在船上偷过黑豆、小米各数斗,又偷得老米、稄米六袋,俱卖给马七分钱使用”。“又陆续偷得老米、稄米三半袋。”
八月,驾漕运船的卢大等八人,“在齐化门号里偷得官口袋七条,又同萧大在船上偷过黑豆、小米各数斗,又偷得老米、稄米六袋,俱卖给马七分钱使用”。“又陆续偷得老米、稄米三半袋。” 道光四年(1824),仍“有偷漏米石”的事情。
道光四年(1824),仍“有偷漏米石”的事情。 十七年(1837),“高碑店、二闸两处”各船户偷米。“且各船户家中,俱有地窖藏匿漕米。”
十七年(1837),“高碑店、二闸两处”各船户偷米。“且各船户家中,俱有地窖藏匿漕米。” 十八年(1838),“各仓漕米出入处所,匪徒串通看街兵役,于粮米车辆必由之处,并不修垫,且故意刨挖深坑,淤泥蓄水,觊觎翻车破袋,向车夫需索搬扛,肆行偷戳,营弁无从过问,街兵包庇分赃”。
十八年(1838),“各仓漕米出入处所,匪徒串通看街兵役,于粮米车辆必由之处,并不修垫,且故意刨挖深坑,淤泥蓄水,觊觎翻车破袋,向车夫需索搬扛,肆行偷戳,营弁无从过问,街兵包庇分赃”。 由于笔者未掌握详细资料,无法统计盗窃漕粮的数量,只能用当时人的话说:“各仓花户向有偷窃之弊。”
由于笔者未掌握详细资料,无法统计盗窃漕粮的数量,只能用当时人的话说:“各仓花户向有偷窃之弊。” 制度弊端之三,回漕。
制度弊端之三,回漕。
一些商贩将京城市场上的米粮,贩运出城,或将本应运到京城的漕粮,卖给漕运官兵、船户及兵丁。这些人就以所购米粮作为漕粮,再运回京、通二仓,称为回漕。张瑞威称:“所谓回漕的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一直是一种谣言。笔者相信,由于北京和通州的漕米价格低廉,间被偷运回南,殊不出奇,但鉴于交通费用的高昂,加上官员的严密监察,贩运的路程不会太长而且偷运量也不可能太大。” 这是他误解了回漕之意,回漕并非将漕粮运回南方,而是回运到北运河沿岸漕船下卸漕粮的必经之地。御史程国仁奏称:“囤贮回漕米石,大半在通州迤南河西务、杨村一带地方。该处系粮运所经,为京内营城稽察不到之地,而运米出京,又总在回空全竣。访拿稍懈之时,各帮运丁,知于抵通前有处买补,遂于受兑时,折色短收。”“奸商贩运牟利,于粮船经行处所,豫为囤贮,运丁等知有回漕米石可以买补,违例多带货物,未能如数受兑,亦属情事所有。”
这是他误解了回漕之意,回漕并非将漕粮运回南方,而是回运到北运河沿岸漕船下卸漕粮的必经之地。御史程国仁奏称:“囤贮回漕米石,大半在通州迤南河西务、杨村一带地方。该处系粮运所经,为京内营城稽察不到之地,而运米出京,又总在回空全竣。访拿稍懈之时,各帮运丁,知于抵通前有处买补,遂于受兑时,折色短收。”“奸商贩运牟利,于粮船经行处所,豫为囤贮,运丁等知有回漕米石可以买补,违例多带货物,未能如数受兑,亦属情事所有。” 道光时,巡视西城御史琦琛等奏称:“卢沟桥附近之黄土铺地方,有奸商贩运接济回漕。”并认为,“京师米价之贵,由于运米出外预备回漕,囤积地方,必不止黄土铺一处,自应严申门禁,以绝其贩米出城之路”。
道光时,巡视西城御史琦琛等奏称:“卢沟桥附近之黄土铺地方,有奸商贩运接济回漕。”并认为,“京师米价之贵,由于运米出外预备回漕,囤积地方,必不止黄土铺一处,自应严申门禁,以绝其贩米出城之路”。 一般来说,凡是回漕的米粮,都非新粮,米色不纯,破坏了漕粮制度。“回漕现象在清代始终存在,屡禁不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运到京、通的漕粮,市场价格竟然会比起运地低,以至于将米粮再从北方带回也能获益。”
一般来说,凡是回漕的米粮,都非新粮,米色不纯,破坏了漕粮制度。“回漕现象在清代始终存在,屡禁不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运到京、通的漕粮,市场价格竟然会比起运地低,以至于将米粮再从北方带回也能获益。”
京城的回漕现象多在嘉庆之后。“凡仓粮出入均归察核,倘该监督等徇情滥收,花户人等,盗卖回漕,及米商、车户囤积包揽,种种弊端。” “朝阳门外,接近仓廒已有开设米局十余处,每年值艘云集之时,向有回漕米之说。”
“朝阳门外,接近仓廒已有开设米局十余处,每年值艘云集之时,向有回漕米之说。” 嘉庆十五年二月,给事中庆明等奏报:“京城稉 [粳]、稄、老米例禁外出,前因京仓所放多被米局收买,包办回漕。”
嘉庆十五年二月,给事中庆明等奏报:“京城稉 [粳]、稄、老米例禁外出,前因京仓所放多被米局收买,包办回漕。” 三月,御史陈超曾奏称:“闻该商贩运米石,先串通经纪,假立发票,票内开写由某处运至某处,以掩盖其出境之迹。实则联车运载囤积乡村,赴天津一带售与漕船。此商人趋利作奸之积习,各仓侵偷米石,借以消 [销] 售,以致漕船得有弥补,遂有恃而兑运不足也。”因“附京居民宜于麦食,其携带升斗之米出城者,亦系卖与商户,图得微利。是商人贩运米石显系回漕”。
三月,御史陈超曾奏称:“闻该商贩运米石,先串通经纪,假立发票,票内开写由某处运至某处,以掩盖其出境之迹。实则联车运载囤积乡村,赴天津一带售与漕船。此商人趋利作奸之积习,各仓侵偷米石,借以消 [销] 售,以致漕船得有弥补,遂有恃而兑运不足也。”因“附京居民宜于麦食,其携带升斗之米出城者,亦系卖与商户,图得微利。是商人贩运米石显系回漕”。 十九年(1814),各旗有驻扎在城外的营兵,还有居住在城外的旗人,他们应支领的米石,“均须由城内载运出城散给”。为了防止这些运出之米石,“影射回漕等弊”,政府特别定章,“凡各旗出米之先,须将城外该营房实驻兵丁花名数目,每名应领米石若干,以及屯居旗人户口应领米石数目,详细分析造册钤用都统印信,咨送本衙门核发各门验放等因,通行八旗都统查照施行”。城外王公大臣所建“园寓食用出城米石”,“随时知照本衙门,由本衙门办给米对牌一分,每分三段,中间一段令领米之人收执,其余两段分交门汛,核对放行。俟出米完竣之日,将对牌缴销。各工程处出城米石,办给照票,令领米之人收执,一张发给门官,一张照验放行,俟出米完竣之日,将照票缴销,以杜冒混之弊”。
十九年(1814),各旗有驻扎在城外的营兵,还有居住在城外的旗人,他们应支领的米石,“均须由城内载运出城散给”。为了防止这些运出之米石,“影射回漕等弊”,政府特别定章,“凡各旗出米之先,须将城外该营房实驻兵丁花名数目,每名应领米石若干,以及屯居旗人户口应领米石数目,详细分析造册钤用都统印信,咨送本衙门核发各门验放等因,通行八旗都统查照施行”。城外王公大臣所建“园寓食用出城米石”,“随时知照本衙门,由本衙门办给米对牌一分,每分三段,中间一段令领米之人收执,其余两段分交门汛,核对放行。俟出米完竣之日,将对牌缴销。各工程处出城米石,办给照票,令领米之人收执,一张发给门官,一张照验放行,俟出米完竣之日,将照票缴销,以杜冒混之弊”。 同年,御史夏国培奏请,“严禁领米兵丁,不得在米铺囤积,及借空房堆聚”。政府认为,这样做多有窒碍。“该兵丁等领米之后,不能独雇车辆,即日运归,势不得不于附近米铺,暂行寄贮,或就肆中舂碓,皆情事所必然”,
同年,御史夏国培奏请,“严禁领米兵丁,不得在米铺囤积,及借空房堆聚”。政府认为,这样做多有窒碍。“该兵丁等领米之后,不能独雇车辆,即日运归,势不得不于附近米铺,暂行寄贮,或就肆中舂碓,皆情事所必然”,  也为回漕创造了条件。二十二年(1817),有吏目朱学斐被派巡查铺户米囤事,便利用职权向铺户讹诈索钱。“将并未逾额米石,先行封禁,串通凑钱打点,怂恿已革巡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分受多赃。”共索“制钱一百四十余千”。
也为回漕创造了条件。二十二年(1817),有吏目朱学斐被派巡查铺户米囤事,便利用职权向铺户讹诈索钱。“将并未逾额米石,先行封禁,串通凑钱打点,怂恿已革巡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分受多赃。”共索“制钱一百四十余千”。 二十三年(1818),太平仓监督长来,刚上任半月,就“听信唐三怂恿,图得贿赂,令已满花户李兴石英入仓影射”。
二十三年(1818),太平仓监督长来,刚上任半月,就“听信唐三怂恿,图得贿赂,令已满花户李兴石英入仓影射”。 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经事中富彰奏称,“有回漕实迹”。“东直门出米甚多,均由各粮店发给,陆续运至长营村地方,再递运至通州城大斗铺,以便上船交纳。又有以羊骨挫灰,拌合粗米蒙混出城。”
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经事中富彰奏称,“有回漕实迹”。“东直门出米甚多,均由各粮店发给,陆续运至长营村地方,再递运至通州城大斗铺,以便上船交纳。又有以羊骨挫灰,拌合粗米蒙混出城。” 十六年(1836)六月,御史万超奏称,“漕粮正额不足,买米回漕”。“有奸商自漕船回空以后,雇觅贫民男妇,升斗肩负,零运出城,至于家卫以南及杨村一带沿途僻静村庄,洒散囤积”,
十六年(1836)六月,御史万超奏称,“漕粮正额不足,买米回漕”。“有奸商自漕船回空以后,雇觅贫民男妇,升斗肩负,零运出城,至于家卫以南及杨村一带沿途僻静村庄,洒散囤积”,  以备回漕。
以备回漕。
三
漕运是政府制定的一项经济制度,是政府集中行政力量进行的资源配置,也是京师粮食供应制度。从其功能和作用看,“京师王公百官禄糈,及八旗官兵俸饷,胥仰给于此”。 正是漕运制度,解决了清朝官兵进入北京后的食粮问题,客观上带给京城百姓所必需的日用商品。因而,清政府继承明代的这个制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统治者的角度看,这个制度在初设时,不仅解决了政府、军队的粮食问题,而且对京城百姓粮食和日用商品的供给,也起到一定作用,无疑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然而,政府推行漕运制度耗费的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各省漕粮不顾程途遥远,糜费帑金运至京师。”
正是漕运制度,解决了清朝官兵进入北京后的食粮问题,客观上带给京城百姓所必需的日用商品。因而,清政府继承明代的这个制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统治者的角度看,这个制度在初设时,不仅解决了政府、军队的粮食问题,而且对京城百姓粮食和日用商品的供给,也起到一定作用,无疑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然而,政府推行漕运制度耗费的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各省漕粮不顾程途遥远,糜费帑金运至京师。” “漕储为天庾正供,每岁征收七省漕粮,连樯转运,自漕运总督以下,分设多官,专司其事,经由大江河湖,运道遇有汛涨浅阻,多方疏导,需费帑金不下数十百万。”漕运“舟行附载南省百货,若遇行走迅速,货物流通,商贾居民,咸资其利。偶值粮艘中途阻滞,则商船均不得越渡,京师百货亦因以昂贵。每年自春徂秋,申诫漕臣疆吏,经营催趱不遗余力。是漕粮为国家重大之务,劳费孔繁,乃趱运如此其难”。
“漕储为天庾正供,每岁征收七省漕粮,连樯转运,自漕运总督以下,分设多官,专司其事,经由大江河湖,运道遇有汛涨浅阻,多方疏导,需费帑金不下数十百万。”漕运“舟行附载南省百货,若遇行走迅速,货物流通,商贾居民,咸资其利。偶值粮艘中途阻滞,则商船均不得越渡,京师百货亦因以昂贵。每年自春徂秋,申诫漕臣疆吏,经营催趱不遗余力。是漕粮为国家重大之务,劳费孔繁,乃趱运如此其难”。 一方面有漕省份的人民需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另一方面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运输,也是不小的负担。对此,政府是很明白的,所以当仓粮爆满时,也产生变更的要求。
一方面有漕省份的人民需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另一方面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运输,也是不小的负担。对此,政府是很明白的,所以当仓粮爆满时,也产生变更的要求。
通常来说,经济制度的推行是政府政治决策的结果。政府在推行制度的过程中也有其规律。仓米存储粮接近爆满时,康熙帝有暂停运粮之意。雍正、嘉庆时,提出实物漕粮改成折征银钱,或折银发放俸粮的办法,实际上都是变更漕运制度的意见,但遭到官员驳议,漕运制度也没能改变。乾隆帝对制度的变更提出了看法,“国家之事,屡次更改,忽行忽止,于体统亦属未合”。 嘉庆帝也认为:“国家立法,皆有一定章程。若辄议变通,必滋流弊。”要求“循照旧章”办理。
嘉庆帝也认为:“国家立法,皆有一定章程。若辄议变通,必滋流弊。”要求“循照旧章”办理。 这说明应维持已确立的制度,不能朝令夕改。后来,乾隆帝又提出:“国家立法调剂,原属因时制宜,非可援为定例。”
这说明应维持已确立的制度,不能朝令夕改。后来,乾隆帝又提出:“国家立法调剂,原属因时制宜,非可援为定例。” 这里又提出了政府建立制度及推行政策的一个理念,即因时制宜。可见,制度在政府看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势而变。且改变一次,也不能成为一个定例,只是因时而已。一般来说,制度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才可信赖,但这种稳定性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调整,否则制度就会僵化。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需要不断修改完善,只不过对于清代来说,一项经济制度的变革是非常缓慢的,需要较长的时间。
这里又提出了政府建立制度及推行政策的一个理念,即因时制宜。可见,制度在政府看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势而变。且改变一次,也不能成为一个定例,只是因时而已。一般来说,制度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才可信赖,但这种稳定性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调整,否则制度就会僵化。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需要不断修改完善,只不过对于清代来说,一项经济制度的变革是非常缓慢的,需要较长的时间。
从本质上看,“漕运制度本身就具有一种反市场、反商品经济的特性”。 正是漕运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在客观上其实已经具备改制漕运的条件,全国粮食流通量较大,不算漕运粮食量,只是民间粮食流通量,估计在6200万石,
正是漕运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在客观上其实已经具备改制漕运的条件,全国粮食流通量较大,不算漕运粮食量,只是民间粮食流通量,估计在6200万石, 供给北京二三百万石粮食,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大臣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同意漕运制度暂时变更,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变革的结果。“围绕着这种制度,已经结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并在事实上成为阻止漕粮改制的重要力量。”
供给北京二三百万石粮食,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大臣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同意漕运制度暂时变更,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变革的结果。“围绕着这种制度,已经结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并在事实上成为阻止漕粮改制的重要力量。” 是时,这类既得利益者,以“俸米岁支最多”的“亲郡王等”,及“各王公家”为主,他们所得粮食“向皆售于粮店”。
是时,这类既得利益者,以“俸米岁支最多”的“亲郡王等”,及“各王公家”为主,他们所得粮食“向皆售于粮店”。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皇亲国戚,和各类高级官员都是权力掌握者,也是利益获得者。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人与商人勾结,更形成了有稳定获得利益机制的官商集团,这一利益集团非常强大,有稳定的暴利获得机制,想改变现实利益,是不可能的。此外,仓场监督,代兵丁支领甲米的领催,仓场中的厂书、花户,值守仓库的兵丁等各类人员,或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或利用职业便利,都在贪污漕粮,已经形成了群体化犯罪。每个与漕运有关的人员,都力图从漕运中得到好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致漕粮制度受到破坏而逐渐崩溃。政府本身最在乎的是权力稳固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即使客观经济条件具备,主观上也不敢轻易完全停止漕运,他们害怕这种经济制度和政策一旦停止推行,将不利于维持和服务该统治集团的利益。正如近代人的评论,“有因此欲折南漕者,则又不可。盖利之所在,民命之所以寄也。使尽去仓储,改归折色,似可杜此弊矣。而商人仍可于米价取赢,食米者依然受困。且皇皇帝都,倘不有此数百万之存储,万分之一,道途有梗,南米不以时至,北方杂粮决不敷用是安坐而待困也。是以仓储之法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改”。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皇亲国戚,和各类高级官员都是权力掌握者,也是利益获得者。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人与商人勾结,更形成了有稳定获得利益机制的官商集团,这一利益集团非常强大,有稳定的暴利获得机制,想改变现实利益,是不可能的。此外,仓场监督,代兵丁支领甲米的领催,仓场中的厂书、花户,值守仓库的兵丁等各类人员,或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或利用职业便利,都在贪污漕粮,已经形成了群体化犯罪。每个与漕运有关的人员,都力图从漕运中得到好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致漕粮制度受到破坏而逐渐崩溃。政府本身最在乎的是权力稳固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即使客观经济条件具备,主观上也不敢轻易完全停止漕运,他们害怕这种经济制度和政策一旦停止推行,将不利于维持和服务该统治集团的利益。正如近代人的评论,“有因此欲折南漕者,则又不可。盖利之所在,民命之所以寄也。使尽去仓储,改归折色,似可杜此弊矣。而商人仍可于米价取赢,食米者依然受困。且皇皇帝都,倘不有此数百万之存储,万分之一,道途有梗,南米不以时至,北方杂粮决不敷用是安坐而待困也。是以仓储之法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改”。
综上所述,政府通过制定制度配置粮食资源,尽管在一定时间内,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时段看,确实也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各朝政府并非固守制度,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地欲对制度做小小的变更,这还是应该肯定的。只是改革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力量之大,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制度的参与者,也是破坏者,他们都为一己之利,欲从制度中得到好处,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从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到借鉴。
作者:邓亦兵,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