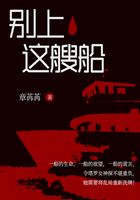
第2章 起航(1)
夏冰身上开始出现奶香味,是在1940年春天那阵子,女儿甜宝带来的体香。
这香气本该出现在妻子杜春晓身上的,然而她总是尽量不碰这孩子,只有在喂奶的时候,才勉强拿起一块布头,把婴儿的脑袋连同自己的乳房都遮起来,就这么撩着衣裳前襟,苦着脸,把乳头塞进甜宝的嘴巴里。这一幕在夏冰看来近乎残忍,因为杜春晓的乳头总是出血。
某一日,杜春晓终于不必再喂奶了,甜宝可以适当喝一些米粥,还会对他笑一笑。可是只要换到杜春晓来抱,她便不停哭,嘴巴张得大大的,似乎亲娘就是个瘟神。所以杜春晓一般情况下都是躲得远远的,看着哭到快窒息的女儿,然后朝夏冰努努嘴,示意他来处理。
荒唐书铺已经不那么荒唐了,它相当低调地开在广州郊外某条摸乳巷里,与青云镇的巷子极像,只不过有了婴儿的气息,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嗅到店主的人情味儿,于是来借书的也多。这里热,杜春晓从未度过如此漫长的盛夏,终日敞着领口,头发冒着浓重的油气,须拿一柄折扇拼命摇动来驱散。桐木柜台烘得温温的,手捂上去,好比捧住了甜宝湿淋淋的后脑勺,又硬又暖。在青云镇积存的湿冷,正一寸一寸地从她身体里抠出来。分娩的辰光,医生就讲过,甜宝的头颅太大,卡在产门上了,要推回去,剪一刀,再拉出来。
当时她以为自己快死了,便恍恍惚惚地点了头,那一刀下去,只听见空空的湿响,也不觉痛。事后,她觉得,应是这里的火热气温驱走了痛感。
那以后,杜春晓便不敢仔细看自己的身体,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抱甜宝。她无法向夏冰解释原因,也鲜少再与他同房。所幸他并不在意这些,甜宝哭闹起来似洪水猛兽,半刻不消停,他忙于应付孩子,也愈来愈少认真看她。为此,她默默松一口气,洗浴的辰光偶尔瞥到肚皮上坑洼如老牛皮,背后便有些发凉,这是她?塔罗牌可没有跟她讲过,分娩是这样子惊心动魄的过程,且后患无穷。
所以杜春晓宁愿长时间待在书铺里,手中握一把牌,鼻孔里微微漾起海水的咸气。港口便在不远处,人人闻得到。这条村里,到处都是与她一样闲散的女人,坐在脏兮兮的港边织渔网,抑或拎鸡仔似的拎着自己的仔,往学堂走去。她们的男人都在海上漂,每次出海好比死别,也不晓得还回不回得来。因未来随时会有变故,她们都憋得面孔焦黄,一张口便有一股咸腥气冲出;唯独二四寨的阿姑们脸皮依旧红白淡出,有一种诡异的嫩光。
所幸,书铺把她们与杜春晓隔开了,界限分明,这些女人再怎么空寂也不会来借一本书,她们多数是不识字的,纵然识得几个,也还达不到看完一部《会真记》的水平。书铺是杜春晓的私人领地,若有人跨得进来,说明他或她都是知心人,也没有必要深聊,只要浅浅几句,淡淡数眼,她便能窥视到他们的灵魂。
这个女学生,两条腿弯弯的,是盆骨撑得太开,必是遇到过不好的事体了;她摆了一张恶魔牌。
那位老先生,很学究的样子,眼镜不停往鼻梁上滑,肩膀缩得很高,必是畏妻的;她摆了一张女王牌。
还有这一位,瘦高个的苍白男子,腰间鼓鼓,应该是藏了一些利器,从黑礼帽檐下边看人,必是来找麻烦的;她摆了一张死神牌。不知道为什么,她隐约闻到了类似玫瑰的芳香。
“杜小姐,上头要我来提个醒,江南人士在这里早晚水土不服,还是要趁早离开。”苍白男子跟她讲这话的时候,唇角不停抖动。该是长年习惯于恐吓之类的工作,已不晓得要如何平心静气地与人交流。
“到哪里去呢?”杜春晓表情木木的,“上天入地不成?”
“上天,你们一家三口都不肯的,还是入地吧。”男子轻轻点头。
书铺后方隐约传来甜宝的哭声,哭得杜春晓心里一紧。
“可地下暂时容不下我们一家人呀。”她强笑了一下,这是生平头一次,她觉得怕。
“难说。”男子拈起她手上的死神牌,反复查看,“也可以到水地去,江海河溪,也是地面上的大洞呀,多少人都埋进去了。”
杜春晓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不响,随手点了一支烟,抓了抓满是油垢的头发。
“就这么定了,谁都莫再倔,让上头放心,你们也放心。”
男子把死神牌放下,径直走出了铺子。
杜春晓拿起死神牌,露出牌底下的两张船票。
“待我们不薄,二等舱。”杜春晓笑了一笑,把船票收进了兜里。
那两张船票,新新挺挺、方方正正,她看了一眼,竟是去台湾的。这令她有些高兴起来,如今世道已是乱到百无禁忌,据说一张票值两根大黄鱼,可见“上头”是不惜血本,要把她剔出自己的地盘。
“为什么要去那样的地方?无如再找找别的方向,甜宝还小,漂洋过海的……”
夏冰讲这话的时候,嘴唇都是白的。
“由不得我们,如今……”杜春晓看一眼他怀里的婴儿,鼻涕口水已糊了她一脸,“算是人家手下留情的。”
她手往衣袋里一插,指头传来一阵刺痛,是船票的一个尖角伤了她。
连夜收拾出两只箱子,跌跌撞撞走到六堡港码头,两个人坐在相邻的两个水泥墩子上,只待天一亮便上船。
夏冰的一只手,轻轻托住甜宝的头,跟杜春晓讲:“她刚才笑了一笑,看见没?”
她站起身,拿出一包烟,走得远远的,站到一个逆风口处,便开始掏口袋找洋火。
咦?洋火呢?竟没有带上?她心里愈加焦躁起来,这已经是今天碰上的第二件倒霉事体了。她的牌便捂在胸口的位置上,硬邦邦的,仿佛戳在了心尖上。
杜春晓事后回想起来,也幸亏是碰上了那位看起来高深莫测的男子,令得她百无聊赖的人生得以重新洗牌。
男子将一支焰色冶艳的洋火递到她面前,她想也不想,垂下头点燃了香烟,深深吸入肺部,再缓缓吐出来,这一记,便把一整日的烦闷都吐光了。
待再抬起头来,才看清男子的真面目。黑礼帽压住眉宇,眼珠子亮得跟狼一样,鼻翼两侧的阴影结了冰,特别深浓,嘴巴好看,两角像上翘的元宝;双排扣的西服像个大塑胶袋,套得松垮垮的,两条腿被下摆遮去了大概有四分之一。
“等船?”
“等船。”杜春晓仔细看他的笑容,总觉得哪里不对,那团火光恍惚间有照亮他脸上的一点小秘密,是什么?
“一家人?”他冲着夏冰与甜宝在夜色中的剪影抬抬下巴。
“不认识的。”此时此刻,杜春晓是真恨不得与那对父女没任何关系。
“福和号不大呀,未曾想还有那么多人在等船。”他又笑一笑。
逆风扑来,杜春晓的香烟灭了,她看着他,没有讲话。
他很识相地掏出洋火,又点了一根。杜春晓这才看清爽了,脸上的“小秘密”系一块朱砂色胎迹,就生在左眼下方,帽子挡不牢的。
“先生,你既知道我在讲谎话,怎么还聊得下去?”
她明白,自己不是那种看起来特别容易招露水情缘的女人,所以只能往不好的地方去想这种际遇,或者是上头的人不放心,派了人来盯着她上船?
男子脱下帽子,竟是光头皮的,惨淡月光把他的脑袋照得清清亮亮。
“不想讲自己的事,都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那先生你呢?想不想讲自己的事?”
他微微笑,那块朱砂的颜色很深很深。
“你不讲,其实我也知的。”杜春晓哑着嗓子笑了两声。
“我不讲,你怎知?”
她将手伸进胸前的衣襟内,摸到了带有体温的那副牌,反正船还未靠岸,玩一下游戏无妨。
男子洗牌的手势,杜春晓很欣赏,他一只膝盖顶在地上,拿另一条屈起的大腿当台面,洗了三次牌,将它交到她手中,手指很长,她能触到他虎口的硬茧。
过去牌——正位的倒吊男。
“原来先生您也是苦出身,一世讲的都是奉献,做牛做马的命。”
她对他满手的茧子充满了敬意。
他不响,只是默默听。
现状牌——正位的隐者,倒位的世界。
“恭喜啊,如今已是功成名就了,只不过出的恐怕是恶名,但是看起来先生你也不介意的。恶名也是名,几多人都是沧海一粟,没看清个样子便被浪打沉下去了。”
她要去翻未来牌的时候,他伸出手,迅速压住她的手背。
“何以见得?”
猜中了?她内心一阵狂喜,本事还没丢尽嘛。
“我怎知呢?是牌这样讲的。”
她自然不会跟他坦白,是那套不合身的西装,那块朱砂胎记,让她起了疑心的;西装不是他的,这个人一世都没有用过真正属于他的东西;胎记形状如凤展翼,她只在哪里瞥过一眼,便永不忘记。
未来牌——正位的皇帝。
她略有些吃惊,这张牌,她选得随意,却总是非常蹊跷地命中了靶心。
“懂了。”
男子直起身来,拍了拍膝上的灰土,背对着她,望向墨蓝海面。
原小凤,绰号凤爷,江苏昆山人士,在上海滩屡犯奇案,包括震惊全国的“中汇银行大劫案”,他带着三个小弟持枪闯入,轰烂了两名收银员的脑袋,把人质一个个吊在银行大门口进行处决,以此换得一辆车,带着两箱金条逃之夭夭。各租界巡捕房耗费了全部人力,却怎么都抓不到他,三天之后,美琪大戏院的幕布拉开,掉下三具死尸,正是他的三名同伙。杜春晓对这桩案子并未挂心,上海滩更大的事体都出过,只是通缉令上的画像却映在她脑子里了,也是去的美琪大戏院,要看美国片《美月琪花》,夏冰去买花生,叫她在门前等一等,她无意中一抬头,正对上通缉令;那张脸,那块朱砂记,便有了印象。
怎么?凤爷也要逃去山高水远的地方?杜春晓松了一口气,因不是冲着她来的,便都不怎么重要,哪怕同船坐的不仅仅是家眷,还有满手血腥的悍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