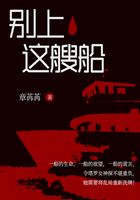
第3章 起航(2)
梁玉棠痛恨坐船,船是她一世的噩梦。
三岁那年,她第一次有了永世难忘的记忆,便是在船上;父亲带她去绍兴,坐乌篷船,桨一摆,水波便往后头一圈圈划开去,她看得欢,两只小手便往水面上伸,身体拗得厉害,两条绵棍似的腿猛一蹬,整个人从老妈子怀里滑脱,落了水。
身体沉入河中那一刻,她浑身发烫,眼睛里边落满了碧绿的水珠。她尚无死亡的概念,只是脑中无故出现了许多的空白点,想掸掉,却越掸越多,口鼻里泛酸,呼吸已近停滞。她只能猛力地摆动着双腿,直到感觉到左脚被什么东西绞了一下,变得滚烫,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所以梁玉棠的童年记忆,便是从“失去”开始的。
那以后,梁森的女儿便打出牌子,绝不走水路。然而这一次,她却穿着齐整,头戴一只挂网纱蓝色礼帽,掩着整张脸,登上了福和号。
上船之前,梁玉棠反复提醒自己,已经长到二十四岁了,没有哪个老妈子抱得动她了,她可以自己走路,虽然得整个身体往右侧倾斜,肩膀耸起,把任何一条平坦大道都当成崎岖路来走。可是至少,她不会再落水了,抑或讲,能避免一切落水的可能性。佩嫂总是把一块帕子,一把短刀,一根尼龙绳,装进随身背的猪皮挎包里;粗壮的臂膀和黑红的面膛仿佛在告诉所有人——她不仅仅是个侍女,还兼任了保镖的工作。
纵使梁玉棠想跳进水里,佩嫂也会用五爪金龙的姿势把她牢牢抓在手里,一如梁森抓着她的命运不放。
清晨的光线模糊中带有一点桃红,梁玉棠远远望住那艘铁锈色的船驶进来,船身磕碰岸沿的时候,她那条残缺的腿都能感觉出一点震荡。更要命的是,还未登船,她已经闻到了脏味儿,讲不出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就是闻起来很脏;是船尾甲板上那些乌黑黑的筐子?站在船顶上冲她淫笑的水手?他们吹起口哨,脸上一律有被海风刮伤的痕迹,粗糙不平的皮肤里挤满了下等人的污垢。
“现在的船,都造得跟野兽似的,又脏又臭,还喷烟。不知怎么会有人愿意待在上头。”梁玉棠望住舱顶上的那两杆大烟囱,皱紧了眉头。
“铁造的,比较稳当,不用怕。”李孟存握紧了她的手。
她一阵恶心,把手抽了出来。她已经能想象上船那一刻,还得踏过那些分不清是油污还是痰迹的东西,路经挤满了平民的三等舱,一步步踏上铁架梯,进入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空间里。一想到这些,她便不自在,无如跳进河里去,让水底的机轮再绞烂她另一条腿吧!
但是她更厌恶李孟存,他生得俊俏又怎样?斯文过了头,为了炫耀留洋身份,还要架一副玳瑁边浑圆眼镜,镜腿插入打了发蜡的、僵硬的鬓角;那发蜡扯紧了他整张面皮,让他看起来比女人还要光洁白嫩。
当初梁森是怎么跟她讲的?
“要不就跟他订婚,要不就自生自灭。”
自生自灭?梁玉棠想笑,她的生与灭若真能自己掌控,倒也是好事。
想到这一层,她便把胳膊往后伸,拔下一只发夹,咬在嘴里,蓝色帽子缓缓从她头皮上滑下来,她抓起快要溜到背上的帽子,用力往福和号的铁梯抛去。
帽子在风里打了两个圈,落到海面上,一直浮着,也不大晃动。
佩嫂想也不想,便要走过去捞,刚跨出一步便扑倒在地,梁玉棠手里那根包银头拐柱紧紧点住了她的右脚脚背。
“去捡。”
“啊?”李孟存怔住了,看看水里的帽子,再看看未婚妻。
“去捡啊,别耽误了上船。”
船上的水手们口哨更响了,笑得震天动地。
“小姐,要不要帮你捡啊?”
“捡了要有奖赏的。”
“奖什么?”
“一个KISS啦。”
“做你的大头梦啊!”
几只常年进出于妓女身体的阳具在栏杆上磨蹭着,他们就是谁都不放在眼里,是最没有禁忌的蝼蚁。
“去啊!”
佩嫂忍痛站起来,退后,扶住了梁玉棠,二人径直掠过李孟存,登上了铁梯。
上面的水手们叫得更欢了,他们终于发现这位千金大小姐是个跛子,生得细皮白肉的女残废,让他们愈加热衷于意淫。
李孟存咬了一下牙,脱下皮鞋,蹑手蹑脚地踏入浅水区,冰爽的海水让他有一些受用,于是奓着胆子,又往前蹚了几步,可是每蹚一步,帽子便漂远一些。他只得停住,站在原地,将身体微微前探。
头顶有什么东西砸来,如疾风扫过,他吓得一个踉跄,跪倒在水里,抱着头颅不停发抖。
水手们疯狂了,他们拍着手,发出凄厉的尖叫,跟盘旋在尸体上的乌鸦一样。
李孟存抬起头,看着不远处那只蓝帽子,正缓缓压入水浪里。
他蓦地听见,一众尖笑里有梁玉棠的声音,“嘎嘎”的,比恶魔更肆意。他咬紧了嘴唇,下意识地将手伸进西装内侧口袋,掏出一块帕子,随即怔了一下,将帕子放回去,拿衣袖擦了擦眼镜上的水珠。
“真是处处有戏看。”
梁玉棠身后的女人在说话,她转过身,看着对方。那是个奇怪的女人,头发胡乱地挽在后脑勺,穿着烟灰色对襟长袍,因为长久不洗的缘故,几乎看不出布料材质;面目略有些臃肿,眼睛倒是很亮,乳房应该很大,几乎快要戳破绷紧的袍子。她皮肤并不太好,但又不像是常年劳碌落下的隐患,更似疏于涂面霜的结果,口脂也剥落了大半。这个女人身后的男子倒是面皮白净,只是黑眼圈特别重,看起来很累,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下等人!
梁玉棠当即给出了判断,对于不穿丝绸的人,她都不放在眼里。
“别多话,快走啦。”
夏冰拿脚踢了踢杜春晓的脚后跟,杜春晓仍是笑嘻嘻的,指了指梁玉棠:“要她先走上去呀。”
梁玉棠气极,欲抬脚,身体却在下坠,所幸有佩嫂托住。
“人蠢的时候可断不能去欺负别人,尤其还是行动不方便的金枝玉叶。”杜春晓笑得更开了。
佩嫂在后头狠狠瞪了杜春晓一眼,提一口气,架住梁玉棠,将她硬往上推去。
杜春晓回头冲夏冰挤了挤眼,他忍着怒气,别过头去不看他,这一别头,便见着底下还在水里扑棱的李孟存,一手拿帽子,西装浮在海面上,里头的绸衫也是湿淋淋的,紧贴胸膛,头发上还挂了一缕破渔网。
水手们的笑声几乎要冲破云霄。
去死!去死!去死!
梁玉棠心里只想到这两个字,事实上,她的毒咒总能实现:十岁那年,在学堂里听课,身边的女生只看了一下她的腿,便转身去跟另一个女生交头接耳,她默念这两个字,没多久两个女生便从学堂里消失了,听闻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敲烂了脑袋,剥下裙子,光着下体挂在电线杆上,死相惨不忍睹;十四岁那年,初潮,医师登门诊治,也是架一副眼镜,鼻尖高高的,听诊器滑过她的胸间,她的心亦跟着猛跳了一下。去死……她竟也发出这样的心声。次日,医师的尸体体石库门底下被发现,一双手都被砍去了;十八岁那年,她迷上了爵士乐,终日摆弄唱片,请了一个乐队到家里来给她庆生;那黑人钢琴手好死不死喝了些酒,连续弹错两个音,她当即便希望他“去死”。如其所愿,钢琴手未走出她的宅子,便死在花园的水池里,额上开出了一个血洞……
眼前这个女人的下场,也一定要如她所愿才好。
所以梁玉棠奋力抬起那条完好的腿,往上迈出一步,又再迈出一步。她相信,很快地,跟在后面的几个孽障就会被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