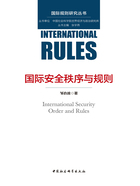
第三节 国际秩序的定义与内涵
一 国际秩序的定义
国际秩序是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国际政治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学术研究成果。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关于国际秩序的统一定义,更没有一个能够用来评估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12]中外学界对国际秩序的定义存在较大分歧。袁鹏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通过主要国家的斗争与协调而形成的规范重大国际行为的原则、机制的总和。[13]显然,这是一个针对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状态给出的定义,符合现代国际秩序标准,但欠缺历史格局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蔡拓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所形成的特定的规范、制度、格局与体系。[14]这一定义提出国际行为体作为国际秩序的行为者,准确把握了国际秩序定义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将格局、体系这些与秩序具有不同含义、处于同一层面的概念纳入秩序定义则是不合适的,且存在大概念与小概念问题,如制度与规范。唐世平认为,秩序是“一个社会系统内的可预测性(可预见性)的程度,而这种可预测性通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行为体的行为、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结果均受到了一定的调控。”“国际秩序就是国际系统中的秩序”。[15]这个定义引用可预测性一词描述社会系统是一个创新,但用来定义国际秩序则含义不清晰。该定义注重国际秩序存在的结果,但没有对其构成要素和其内在核心要义进行精确描述。
阎学通在总结中外学者对国际秩序定义基础上,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状态”。并特别强调,“该定义明确了国际秩序的本质是无军事暴力行为。明确不使用暴力,可以为人们判断一个时期有无国际秩序提供最基本的标准”。[16]这个定义将“国家”定义为国际秩序的行为体,符合现代国际秩序范式,将“国际规范”引入国际秩序定义,也抓住了其核心要素。但这一定义有关暴力问题的处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将“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引入定义,将暴力因素排除在国际秩序定义之外,实际上这是将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惩戒机制排除在外,因而这一定义是不准确的;第二,将“不使用暴力”作为“有无国际秩序”的标准,则显然与历史史实不符。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作为例子,就能非常直观地看出这一定义存在的上述两个问题。现有国际秩序是以各主权国家为国际行为体,以《联合国宪章》为主要国际规范,以安理会决议及其行动作为惩戒机制的集体安全秩序。其中,安理会负责对包括武装侵略等非法使用武力的情况做出包括军事反应等强制措施在内的决议并开展行动,也就是说现有国际秩序含有暴力方式和暴力行为。若按照上述定义,就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产生认知偏差:一是含有暴力因素的安理会体制就不应该是构成现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安理会体制恰恰是现有国际秩序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比如,在1990年8月伊拉克以武力吞并科威特这一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联合国会员国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根据这一决议,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出兵海湾,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恢复了科威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国际正常秩序。这是现有国际秩序采取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典型案例;二是因为现有国际秩序含有“使用暴力”因素,若按照阎学通的定义,那么就可以认为现在不存在国际秩序,这显然与国际政治现实不符。
布尔将国际秩序定义为“维持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模式”。[17]布尔的定义将国家社会也纳入国际秩序含义中,显然将国家内部秩序也纳入国际秩序范畴,这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秩序的目标和现实不符;同时,这一定义对维持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没有给出清晰的含义,没有触及秩序含义的本质即有条不紊的状态;而且,布尔对国际秩序的定义最后归结为一种模式而非状态,没有体现国际秩序定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18]
为了对国际秩序提出准确的定义,首先有必要对国际秩序中的两个关键词——“秩序”和“国际”给以准确的理解。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现代汉语词典》将“秩序”解释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19]。《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将“秩序”(order)解释为“社会政治体系的一种特定范围或方面、规律或和谐的安排”。[20]
“国际”一词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凡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应是国际关系。当然,“国家”一词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从一般国际法看,只有国家才具有承担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21]现代国际秩序也是以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然而,我们对国际秩序的定义,不应该仅是对现代国际秩序的定义,而应从人类波澜壮阔的悠久历史的宏大角度来认识和定义,也就是说,对国际秩序的定义应具有历史格局,这样也才具有学术的普遍意义。因此,历史地看,凡是能对一定数量的居民、一定规模的领土拥有排他性管辖权的政治单元,都应看作是国际行为体。[22]这样,古代以前的帝国、王国、公国甚至一些较大的部族等符合这一定义的政治单元都可称为国际行为体,它们在所在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秩序都应看作是国际秩序。因为,古代形成的这些秩序确实具备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具有国际秩序的特征。如此,就可将古代形成的多个地区性国际秩序纳入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范畴,这扩展了国际秩序研究的宽度。广义地看,国际秩序也并非仅指作用于全球的世界性秩序,如凡尔赛—华盛顿秩序、雅尔塔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等,国际秩序也包括在各地区、在某领域内形成的各种多边秩序,如在欧洲形成的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秩序,在东南亚形成的以东盟为核心的东南亚政治经济秩序,以正在谈判并即将达成的中日韩自贸协议为核心的东北亚经贸秩序等。这样,该定义即扩展了国际秩序研究的广度。
综合国际秩序内含词语的本意和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本书认为秩序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单元共处一个体系内,按照一定规范发生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状态。国际秩序的定义就是:“各国际行为体在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内,按照普遍或共同认可的国际规范发生关系而呈现出的状态。”
二 国际秩序的内涵
对于一个定义,首先需要对其中词意进行深入阐释,这样才能使人对该定义有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在上面给出的定义中,第一个关键词是“国际行为体”。前面已对“国际行为体”进行了明确定义,即能对一定数量的居民、一定规模的领土拥有排他性管辖权的政治单元,它能在所处的国际体系内拥有权利并能承担对该体系和其他政治单元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广义的国际行为体概念,不再局限于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国家概念,而是将所有历史上符合这一标准的政治单元都视为国际行为体,这就扩展了考察、研究国际秩序的历史视野。
其次,需要对定义中国际行为体所处国际体系这一概念的理解。“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23]国际体系是指国际行为体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国际秩序是有一定范围的,既可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也可是地区性的、区域性的,关键要素是这些政治单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而共处于一个国际体系内。而这个国际体系外的政治单元,并没有与体系内政治单元相互联系,则不是这个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比如,朝贡体系内的东亚秩序,东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西亚国家、欧洲国家、非洲国家等,与东亚国家很少联系或没有保持常态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因而也就不是东亚秩序的一部分。东亚秩序是一种地区性国际秩序。
再次,需要对另一个关键词“国际规范”进行明晰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对“规范”的定义是: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24]把“规范”含义引入国际秩序概念中,“国际规范”的定义就是为体系内国际行为体所普遍接受并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行为标准。国际规范包括原则、规则和长期形成的国际习惯等。原则和规则一般载入相关国际法律文书,是明文规定的国际规范,这很容易理解,而国际习惯则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国际规范,一般不太好理解。但国际习惯曾一度是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现在仍然是国际法的主要和重要渊源之一。[25]国际习惯是一定数量的国家经过一定时间形成的具有一贯性的广泛行为(模式或标准),是国家通过其实践体现出来的、对某一或某些规则具有国际法效力的“默示”承认。一项国际习惯一旦成为国际法的一般规范,它就约束所有对之不加以反对的国家。[26]比如,前面提到的东亚秩序,虽然没有东亚国家、部族共同签署的法律文书,但中央王朝与其形成的朝贡关系格局和遵循的行为规范,却是被各方在上千年历史中所普遍接受并遵守的国际习惯,这种国际习惯就是一种国际规范。
最后,定义中国际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普遍或共同认可,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义。比如,被誉为现代国际秩序始端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后来的维也纳秩序,其中的国际行为体只是欧洲等西方国家,只有他们是这种国际规范的制定者、接受者,而其他大洲包括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广大国家则是局外者,这些国家从未认可、接受这种国际规范,西方国家也从未按照这种规范对待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因而亚非国家并不是这种秩序的国际行为体。因此,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维也纳秩序只是欧洲秩序,是一种地区性国际秩序而非世界性国际秩序。
这一定义不仅可涵盖世界上各个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多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也覆盖了当今世界在各地区、区域在各领域形成的多个多边秩序,具有历史格局和丰富含义,拓展了国际秩序定义的宽度和广度。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应承认历史上在不同地区形成的国际秩序,而非以现代国际秩序观来认识、评判古代各地区的国际秩序,这也有利于我们研究当代及未来世界不同的多边国际秩序。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全面、完整而清晰的对国际秩序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