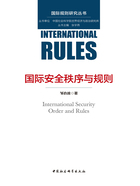
第二节 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要正确理解和准确定义国际秩序,弄清其中的构成要素则是关键。目前,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外国学界,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的认识均有较大分歧。2014年7月2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召开了国际秩序的专题研讨会,学界的资深学者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定义等均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些认识或定义无疑集中并代表了中国最高层次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关国际秩序问题的最新看法。[8]但学者们提出的有关国际秩序构成要素不仅不尽相同,而且还比较分散、宽泛,将原则和机制、价值观和道德、格局和体系、权力和权势、文明因素和经济力量等十几个因素都纳入了国际秩序构成要素中。显然,将过于分散、宽泛的因素纳入国际秩序构成要素中,使得我们一方面无法清晰准确地定义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也无法抓住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把握国际秩序的本质。
阎学通在总结以上中国学者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秩序构成的三个要素: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9]外国学者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同样存在分歧。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为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和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这两个因素视为国际秩序构成要素。[10]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则把共同利益、国际规则和制度这三个因素视为国际秩序构成要素,认为国际社会的“秩序不仅是有一组条件的结果,也是关于共同利益、行为规则和制度这三者观念的结果。共同利益的观念基于社会性的基本目标,行为规则的观念用于支持这些目标,制度的观念则有助于使规则有效率”。[11]显然,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的看法不尽相同。
所谓事物的构成要素就是事物存在的最基本因素,离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事物都不可能存在。从国际秩序的渊源和目的、国际秩序的历史演变及其实践看,本书认为,国际秩序主要有以下三个构成要素:国际行为体、一套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和相应的惩戒机制。首先,国际行为体是国际秩序的行为者,有它们的参加才能构成国际秩序的最基本要素,只有秩序范围内的行为体特别是主要行为体均参加到秩序中,这个秩序才可称得上是国际秩序;其次,需要有一套为各行为体所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以让各行为体遵守,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最后,也要有对违反规范的惩戒机制,以维护规范的有效性,这样才能使国际秩序真正运行,否则国际秩序就会有名无实而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秩序,这也是构成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此可见,国际秩序由以上的基本要素、核心要素和必需要素构成。
实际上,任何秩序的构成要素都有这种共性。比如,一个社会秩序,人的存在是前提,没有人就无所谓社会秩序。然后要有约束人行为的法规,供大家遵守。归根到底人是群居性动物,若没有法规,社会就会杂乱无章,也就没有社会秩序可言。但有了法规也不能保证社会就会有序运行,如果大家都肆意违反法规而得不到惩戒,社会仍会陷入无序状态而相当于没有秩序。这就需要有法院等机构对违反法规者进行惩戒,以维护法规的有效性,保障社会的有序状态。因此,构成一个基本的国际秩序,国际行为体、国际规范和惩戒机制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有了这三个要素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国际秩序的三个构成要素特别是国际规范和惩戒机制,有时是明确的或者明文规定的,有时则是无明文规定但是约定成俗、得到各行为体普遍认可、遵守的,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这一国际秩序的形成及其有效运行。比如,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就存在一个朝贡体系及相应的东亚秩序。在这个东亚秩序中,中国和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暹罗、占城等中国的一些周边王国、部族等,是这个国际秩序的行为体,它们基本都参与到这一东亚秩序中。中国保持对其他王国、部族的宗主国地位,但并不实际干预其内部事务,各方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王朝上表纳贡,以表示在政治上认可、尊崇中央王朝的中心地位,中央王朝也以“薄来厚往”礼遇优待各方。各方在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中,不仅可于政治上获得有力支持、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且文化得到极大提升,故而在朝贡体系中获得很大实际利益。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王朝与各周边王国、部族就形成了一种关系格局并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虽然各国没有就此签署法律文书,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各国普遍接受并遵守这一东亚秩序的国际规范。一旦出现王国、部族破坏上述规范的行为,如挑战中央王朝权威、军事入侵他国、发生内乱后请中央王朝干预等,中央王朝就会凭借其强大实力对此予以干预制止,以维护朝贡体系的稳定,这就是东亚秩序的惩戒机制。虽然这一东亚体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但也是一个较为完整稳定的古代国际秩序,这个秩序维持了东亚地区上千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
相反,具有现代国际秩序特征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虽然建立了国际联盟组织,也确定了《国际联盟盟约》这一国际规范,但从国际秩序构成要素看则存在重大缺陷:一是国际行为体参与度不足。秩序范围内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行为体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苏联直至1934年才加入);二是惩戒机制效力不足。虽然秩序内建立了对会员国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发动战争等非法行为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制止的集体安全机制(该盟约第十六条),但由于该盟约机制内在的相互牵制和英法大国对立的现实矛盾,该集体安全机制的执行效力大为减弱,在随后几年未能有效地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日本侵略中国等违反《国际联盟盟约》的重大行为做出惩戒反应。也正是由于存在重大缺陷,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最终未能阻止再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以说,凡尔登—华盛顿秩序构成要素的先天不足,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国际秩序。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秩序中的惩戒机制存在效力受到限制的先天缺陷,这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属性决定的。由于没有一个凌驾于世界各国的世界政府,也就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主权之上的强制性法律执行机构,因此,国际惩戒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只能依靠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参与和配合,需要他们为此提供公共产品。这样,惩戒机制的效力就由各国特别是大国的态度所决定,也就由这些国家的政治立场、利益取舍所决定,这就决定了惩戒机制效力的有限性。比如,就较为成熟完备的现有国际秩序而言,其惩戒机制是集体安全机制,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并予以实施。而安理会能否有效行使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害国际安全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职责,则受制于大国的态度。而大国是根据其政治立场和利益进行决策的,当因某些事项对某些国家进行惩戒不符合大国利益时,特别是当大国自己就是违反宪章的行为者时,拥有安理会否决权的大国就会对此进行否决,安理会就无法对此种行为做出惩罚决议,惩戒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这大大影响了国际秩序惩戒机制的效力。比如,针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安理会决议提案,美国均行使否决权予以否决,致使巴勒斯坦领土被以色列不断蚕食,而以色列并未因此而受到惩罚。针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侵略行为,因为当事国是常任理事国,安理会也根本无法通过谴责和制止的决议,不能发挥制止侵略、维护国际安全的作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票决统计,美苏(俄)两个大国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次数占全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次数的75%,这两个大国的争斗是影响安理会效力的主要因素。
在中外学者关于国际秩序构成要素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如上面阎学通、布尔等著作提出的观点,都将价值观视为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毋庸讳言,价值观在构建国际秩序中发挥着先导和指引作用,特别是对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国际规范起着决定性作用。秉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价值观决定着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属性。但价值观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只有当它化为约束各行为体的具体原则、规则等,体现在具体的国际规范中,才能真正体现其宗旨和意义,这就是价值观在国际秩序中的关键作用。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价值观本身并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而是指导国际秩序建立、决定国际秩序属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建造一座房子,地基、墙、梁柱、屋脊等都是房子的构成要素,要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目标建造房子,则不是房子的构成要素,但理念和目标指导我们建造什么样的房子,建成的房子也是这一理念和目标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