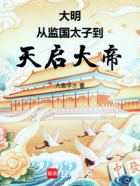
第17章 帝王无情,并非天生
朱由校蹙眉迟疑时,李汝华连忙出言解释:
“殿下容禀,先帝多年不上朝,朝廷地方大量官职空缺日久,致使各省税银征收困难,现在朝廷都难以为继,委实拿不出钱粮赈灾...”
“父皇登基之初,不是补齐了多数官员么?”
“这不刚刚过去一个来月吗?新官到位就是全力以赴征收,加上各地时有匪寇,没这么快收至太仓银库...”
李汝华说得滔滔不绝,朱由校的眉头越来越紧。
前者话刚落音,后者便意味深长追问:“本宫就问一句,现在太仓银库空了?”
李汝华苦着脸对曰:“空虽然没空,但只剩下不到五十万两...”
大明国库只剩五十万?一个贪官家产都不至于。
朱由校虽然内心震惊,却不能对灾情熟视无睹,他清楚朝廷若对灾情不管,流民一多就会产生动乱。
明末著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是从陕西走出来的反王。
想到这里,朱由校试探性问道:“五十万两也不少了,那就先拨一半用于赈灾?应该能买到不少粮食,等到年末各地税银收上,再视情况继续赈灾...”
“殿下!”
李汝华没等朱由校说完,便起身打断并语重心长提醒:“殿下慈悲令人可敬,然而这五十万两是留存开支,先帝定陵修建、朝廷官员俸禄、宫廷用度、宗室禄米、九边军饷等等,很多地方还欠着呢...”
“那陕北旱灾不管吗?”
“应该管,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几乎每天都有紧要的事,旱灾、水灾、风灾、蝗灾时有发生,可现在太仓银库拿不出存银,光九边军饷就欠三百万...”
“所以呢?”
朱由校双手一摊,扬起嘴角追问:“本宫才做三天太子,正式读书读了一天,这么困难的事,李尚书认为本宫能解决?”
此时此刻,他突然想起穿越前,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一个前辈传授经验。
领导时间宝贵,他们只喜欢做选择题,不要让他们做问答题。
把问题和麻烦抛给领导,提问题这人存在什么意义?
李汝华抛出问题,朱由校虽然答不上来,自然选择反客为主。
“呃...”
李汝华被怼得有些尴尬,刘一燝见状立刻接过话腔,笑盈盈说道:“处理国事就是这样,手心手背都是肉,有时候难免需要取舍,太子殿下觉得难办,是初次接触不适应,以后处理多了就顺手。”
“刘阁老有好办法?”
“陕北诸府旱灾两年,交不上税的百姓远走他乡,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银,朝廷如果减免征收,能一定程度劝民返乡,但要调钱粮赈灾,目前确实办不到...”
“既明知办不到,这折子为何到了这里?”朱由校指着李汝华桌案示意。
刘一燝脸上挤出慈祥表情,“这是专为殿下准备的,陛下要锻炼您治国,了解地方情况很有必要。”
“了解又没办法,还不如不了解...”
看到朱由校这般嘟囔,刘一燝又捋髯提曰:“殿下仁慈,若想赈灾,尚有一法。”
“何法?”
“内帑尚有不少存银...”
听到此处,朱由校总算听明白了。
这俩家伙拿出这灾情,就是奔着花内帑(tǎng)的钱。
(内帑,区别于国库,属于皇帝、皇室的私财、私产。)
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
只有真当了皇帝才清楚,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就像李汝华刚才所言,国家方方面面都要用钱,皇帝花钱也会被各种限制,每个时代都有类似内帑的机构,一是为了方便皇帝花钱,二是不让皇帝向国库伸手。
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所产出的资源相对有限。
而自从产生王朝开始,朝廷与地方一直围绕资源分配做争斗,明朝此时出现入不敷出,主要是地方与背后势力,拿走属于朝廷分配份额的结果。
嘉靖操纵巨贪严嵩秉政,本质上也是不满地方拿得太多,皇帝通过‘以夷制夷’的办法,勉强维持着大明分配的平衡。
而万历的做法更直接,派出矿税太监到地方收税。
在产出资源相对不变情况下,万历多拿则地方就必定少拿,双方为了利益都疯狂盘剥百姓,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增,君臣矛盾也十分尖锐。
万历驾崩之后,内帑留下一笔财富。
朱常洛继位之初,已从内帑调了一百万银,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现在户部也打起了主意。
......
朱由校作为历史爱好者,对明末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清楚刘一燝、李汝华的心思。
小聪明花我头上,你们是不是想多了?
钱攥在朱常洛手里,我说话不算数且做不了主,好好‘陪太子读书’不行么?
酉时末,晚课结束,天色昏昏。
朱由校回慈庆宫路上,还在想陕北旱灾这件事。
其实李汝华说得没错,明朝两京一十三省这么大疆域,几乎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受灾受难也是常有的事,如果把每件事都当要事办,这国家反而容易乱套。
帝王无情,并非天生。
大多是被逼出来的,也有经历太多而麻木。
朱由校不一样,他穿越前只是个普通人,此时还没练成铁石心肠,听到灾情很容易共情。
所以回到慈庆宫,魏朝前来询问学业时,朱由校便主动询问府上开销情况。
他可不想铺张浪费,然后也伸手向内帑要钱。
魏朝闻言先一愣,跟着解释道:“按旧制,每年年底户部核算支出,然后年初拨付禄米与现银,但万岁爷刚刚登基,殿下册立也才三日,老奴在内帑先支了一万两,暂时用作日常生活开销,相关账目都有记录,殿下随时可以查账。”
“本宫不查账,就是想到了问问。”
朱由校微微颔首,又好奇追问:“每年会拨多少禄米与现银?东宫的支出情况又是怎样?正常能够收支平衡吗?”
“每年大约折银十万两出头,正常的支出无非衣食住行,十万两肯定是够用的,就怕特殊情况产生巨大开支,不够就得求助万岁爷,然后从内帑补贴一些。”
魏朝说得很平淡,而朱由校讨厌伸手,于是蹙眉追问:“特殊情况?比如呢?”
“比如宫殿大修,以及殿下将来的冠礼和婚礼,都是花钱较多的地方。”
“婚礼?”
朱由校一脸错愕,太子结婚要自己筹钱?